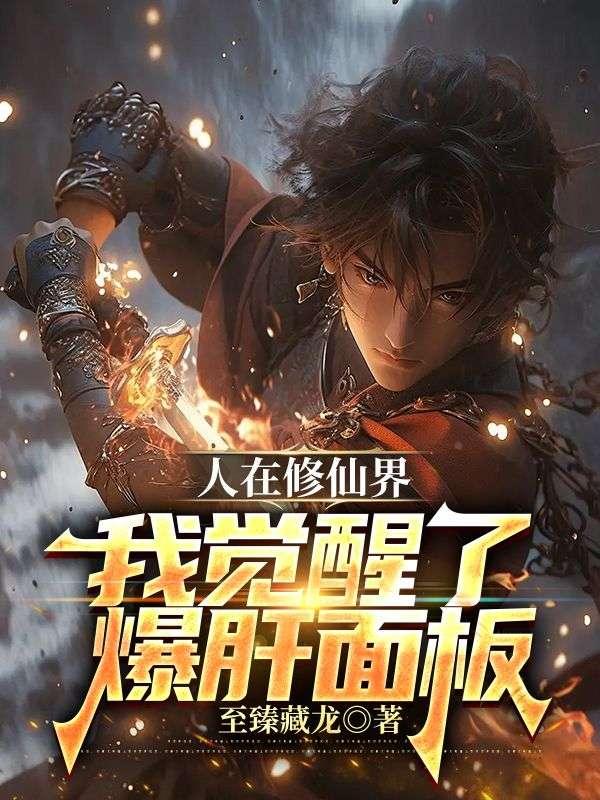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荒唐公主的怨种姐妹重生后 > 7080(第18页)
7080(第18页)
所以这门婚事齐山玉就算是听都没听说过,他也要娶进门来。
“说是那齐山玉很不情愿。”永安说的眉飞色舞,道:“他嫌弃那新娘子是东水一武将家里出来的,身份低微不说,人也不曾读过书,只是受父命难为,将人接进了门来而已,却以战事繁忙为理由,多日不曾回府门,连婚事都不曾办过,也从不曾让这姑娘出门,连交际都不让她去。”
按着寻常规矩,姑娘既然进了门,就该请族老主持婚事,操办一场,但齐山玉连府门都不回,这婚事也就这么僵在这里。
这位姑娘的位置便十分尴尬。
顿了顿,永安又补了一句:“这姑娘能被送过来,是因为前段时间东水水患的时候,齐山玉的父亲,齐老大人去镇压,被卷进流民纷争里,这位下属拼死救人,落了伤残,他本就是武将,落了伤残就要退,以后只能做个闲职,恐怕再难上进,齐老大人念他的恩情,所以才将这姑娘送来长安的,以这门婚事,保了人家全府富贵。”
下属的门槛低,以婚事相抬是最方便的,联姻,是这天底下最有效的提拔方式,只要联姻了,这就是一家人,两家的资源都是互相流通的,所以女子要上嫁,男子要上娶。
只是女子上嫁受的委屈与男子上嫁受的委屈又完全不同,前者在婆家受尽磋磨,在产房伤筋动骨,好处却都给了自己父母兄弟身上,外人还要赞叹她好命,而男子却能直接吃到妻子的血肉,登高梯、上青云,以后有权有势了,再纳妾也是在所难免。
男女的不同在这桩婚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位上嫁而来的未婚妻眼下是居住在齐府,但住的也是如鲠在喉,齐山玉看不起她,不给她脸面,眼下齐家的族老还在,齐山玉就这般冷待她,以后齐家族老走了,这位未婚妻还有立足之地吗?
但她若是受不了委屈走了,以后她的父弟怎么办?她的父亲已经为了救齐老大人而重伤留疾了,爹不行了,他们家就摇摇欲坠、撑不住了,都靠着她这个长女的姻亲活着呢,她又有什么办法?明知道惹人生厌,也只能硬咬着牙留下。
宋知鸢听着都替她叹息。
人生而为人,却要被条条框框困在各种宅院里。
“她难有好日子的。”宋知鸢莫名觉得悲凉,为这位从不曾见过面的女人,她看向与她近在咫尺的永安,低声说:“若日后有机会,我当帮帮她。”
“你如何帮她?”永安不明白宋知鸢为什么要帮她,在永安眼里,宋知鸢跟齐山玉结了仇,那宋知鸢跟齐山玉的妻子就也结了仇,既是仇人,又为何要帮她?又如何来帮她?
“以前我也差点是她,所以难免可怜她。”宋知鸢抬手,摸了摸永安的脸,道:“至于如何帮她,这些道理,我做官后便懂了。”
不,应当是掌握权力之后便懂了。
最早时候,大陈是不允许女人出去立门户的,女人名下不能有任何财产,就算是给的陪嫁,也得记挂在族里、父兄名下,亦或者丈夫名下,女人不能做上税,那她们就不能做生意,就算是做,也得拉个男人来挡在前头,地契或房契上,她们的名字也不允许出现,所以钱财从来都与女人无关,而一旦依靠的男人没有了,女人就会沦为被争抢的战利品。
因为国家不允许她们比男人更高,所以她们只能跪在地上任人摆布,女人就只能做宅院里的东西。
早些年,太后曾允女子出去立女户,允许女人自立门户,自己名下有财产,自己出去做生意,从那以后,女人出嫁的钱财,才算是真的属于自己的钱财。
早些时候,宋知鸢太小,不知道这其中的深意,现在想来,太后才是那个真正吃够了男女之间的苦,所以一门心思照拂女人的人。
人皆苦,人皆难,所以宋知鸢不想去为难这些在苦难里浸泡的女人,她只是低低的叹了一口气,道:“男人们已经吃尽了好处,我们女人就不要互相为难了。”
她枕在木桶上的手已经有点发麻了,干脆顺势站起身来,一边起来一边轻声说:“若是天底下的女人都能做官,那才是好事。”
但若是男人来当皇帝,一定不会去体恤女人。
就像是长公主不会真的将她院里那些男宠当个人来一样,永安以前把那些男人当成人来看了吗?没有,她只把和她同样身为女人的宋知鸢当成人来看。
永安这样对别的男人,那别的男人也会这样对女人,这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只是本能而已,所以没有什么谁体恤谁,只有谁在上面,谁才说了算。
永安不太能明白宋知鸢的悲悯,但她敏锐的察觉到宋知鸢低落情绪,所以她连忙说道:“你莫要不高兴,以后待有机会,我开了女子做官的先河便是。”
宋知鸢当时从浴桶里爬出来,闻言笑道:“你?还是等太后回来开吧。”
当初她去讨官,有润瓜这种神仙作物在手,都被一群官员埋汰的抬不起脑袋,将她逼迫到撒泼骂人的境地,最后还是靠着太后才能将这浩瀚官途撕开了一条缝,让她硬挤了进来,而永安什么功绩靠山都没有,她如何能去给所有女人开一条路?
永安哪里扛得住啊?这满朝文武活吃了她。
“我还有弟弟。”永安理所当然道:“他会听我的话的,他可是皇帝。”
宋知鸢脸上的笑意淡了点。
她都不敢想永昌帝掌权之后,她自己会是个什么光景,永昌帝会爱永安,但爱不到她头上去,以后就算是有了同等的功绩,也一定是先把机会给男人。
她底下少了个根,脑袋就挺不直,也没法子。
但那些事儿都离她太遥远啦,她没有继续提,只道:“好啦,泡够了,我们一道儿睡觉吧,明日辰时,廖家军将来,你还要去和那些人和谈呢。”
之前永安决定来议和之后,北定王这边就派了信使过去,与廖家军约见。
他们双方都不肯去对方的地盘,最后在两军交战的最中心,搭出来一处帐篷,双方都不得携带亲兵,不得携带武器,只能单独见面。
长安城这边是长公主与小侯爷出席,沈时行回避,北定王同行,廖家军那头是廖寒商带着两位心腹出席,小皇帝与太后都不曾放出来。
也就是说,这帐篷里最多只会有六个人来商议割城一事,永安就是其中之一。
她得好生休养。
永安“嗯”了一声,爬到旁边榻上,俩小
姑娘一人一个厚厚的棉被,面朝面的睡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