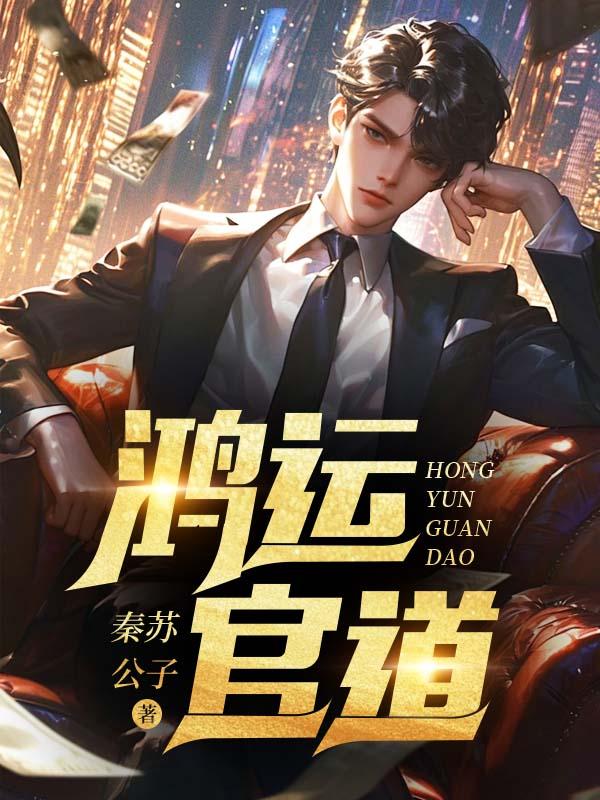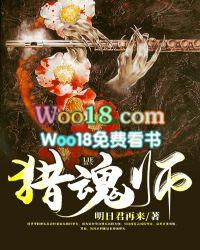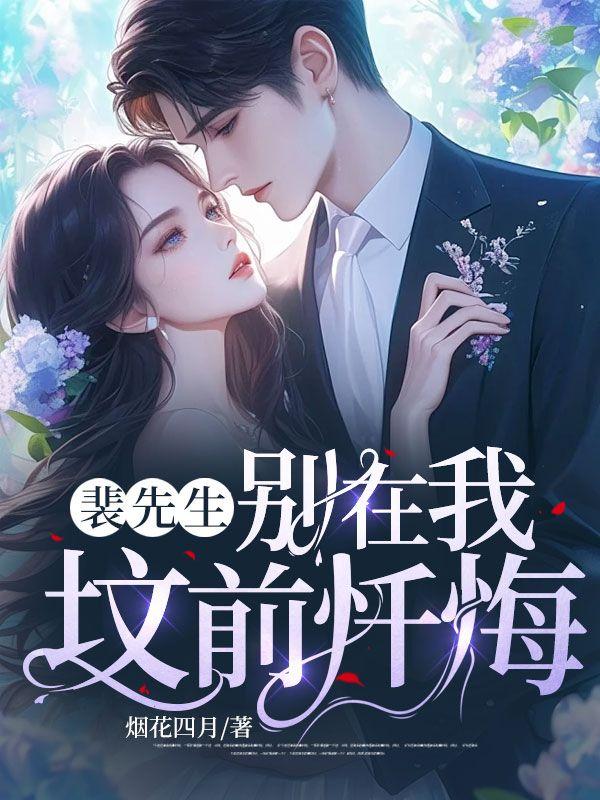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次元入侵:我能垂钓诸天 > 第485章 神秘四奥和常规的奥特曼完全是两个概念(第3页)
第485章 神秘四奥和常规的奥特曼完全是两个概念(第3页)
叶辰没有回答,只是将手按在水晶上,低声说:“我只是一个想把热水端给狐狸的人。”
话音落下,水晶爆发出刺目光芒。
全球同步现象再次降临。
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突然黑屏,浮现出一段手绘动画:一个小男孩蹲在雨中,试图用破伞遮住流浪猫。镜头拉远,整座城市逐渐化作森林,高楼变成巨树,车流变为兽群,人群脸上褪去冷漠,重新长出好奇与温柔。
伦敦地铁隧道内,一名盲人乘客手中的导盲杖突然生根,钻入地面,瞬间开出一片发光藤蔓花海,照亮整条线路。乘客们自发关闭手机,静静欣赏这无名之美。
印度恒河边,一位老妇每日焚烧亲人骨灰的习惯突然停止。她开始用花瓣和歌声代替火焰,并告诉旁人:“他们不需要升天,他们一直都在听着呢。”
而在太空,国际空间站宇航员惊骇发现,地球周围那层“情感辉光”正在向外扩散,形成一条螺旋星带,直指半人马座方向??似乎在回应某种等待已久的召唤。
三个月后,第一艘搭载“共感舱”的探测器发射升空。舱体内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只有一株活体苔藓、一小碗温水、一根青铜莲花钓钩,以及一封手写信:
>“致未知的朋友:
>我们还不完美,但我们学会了倾听。
>如果你们也曾失去过谁,请让我们一起找回。”
探测器进入深空第七日,接收到一段编码信号。解码后,竟是地球上早已灭绝的渡渡鸟叫声,混合着毛利语祷词和婴儿啼哭。
人类终于明白:宇宙并非冷漠,只是需要正确的语言。
叶辰最后一次出现在世人视野,是在蒙古草原的一个牧民帐篷里。那天暴雨倾盆,闪电劈开乌云,照亮他平静的脸。他正教一个五岁女孩如何用羊毛绳绑出“心结”,告诉她:“这个结不会解开,但它能让两个人的心越靠越近。”
第二天清晨,帐篷还在,人已不见。
只留下一本笔记,扉页写着:
>“我不再是垂钓者,因为我终于成了鱼。
>当你看见水面涟漪,请记得??
>那是我游过的痕迹。”
多年以后,孩子们在学校学到一门新课程:“情感考古学”。他们学习如何从废墟中提取未说完的话语,如何用日常物品重建失落的联系,如何判断一片土地是否还“记得爱”。
而在每一个春分与秋分的七分钟静默时刻,无论身处何地,人们都会停下手中之事,轻轻敲击金属物件一下??那是新的摩尔斯密码,代表“我还在这里”。
某年冬至,南极科考站再次收到冰晶信件。这次纸上浮现的是一幅画:两个身影并肩坐在湖边,手持钓竿,水中倒影却是漫天星辰。
背面只有一行字:
>**“故事讲完了,轮到你了。”**
无人知晓是谁送来此信。
但当晚,全球新生儿第一次啼哭的时间,惊人同步。
医生们记录下这一现象,命名为“共感原初律动”。
而在某个偏远山村,一个刚学会走路的toddler摇摇晃晃走到灶台边,踮脚拿起母亲煮好的一碗热汤,蹒跚走出家门,放在门前石阶上。
母亲追出来问:“你在做什么?”
孩子回头,认真地说:“等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