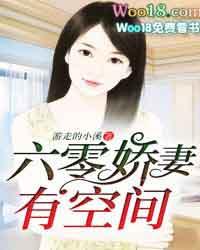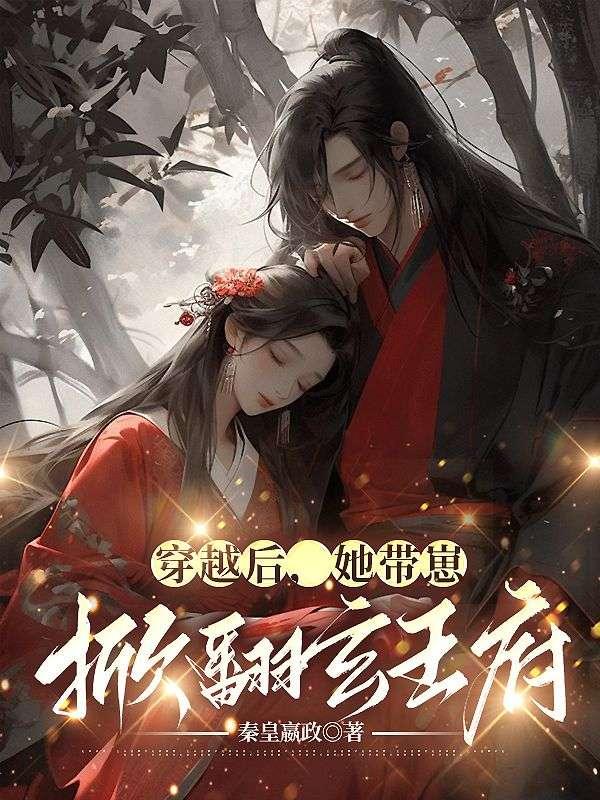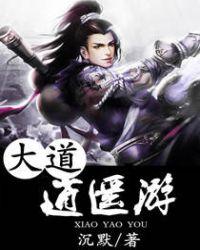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的哥哥是高欢 > 第267章 征服女人的方式(第1页)
第267章 征服女人的方式(第1页)
高羽虽说脱身了,但离开时元淼那幽怨的眼神,让高羽明白过来……
一场恶战注定是避免不了。
分身乏术。
女人多,子嗣多,高羽根本就照顾不过来,总会有疏忽的地方。
他也唯有尽力而已。。。。
腊月二十,恒州城外的雪仍未停歇。北风卷着碎玉般的雪花,在田埂与沟渠间翻飞,仿佛天地之间只剩一片苍茫。然而就在这严寒之中,数百名农夫仍顶着风雪,在北原屯田工地上挥动铁锄,破开冻土。他们脚踩草鞋、身披麻布斗篷,脸上结着霜花,却无人退缩。每一声凿地的响动,都像是向命运宣战的鼓点。
高洋立于高台之上,手握一卷《冬闲垦荒指南》,身后是新设的“民命司”执事官与农学堂教习。他并未穿厚裘,只着寻常紫袍,肩头积了薄雪也不拂去。杜丰劝道:“大人,这般风寒入骨,您久站恐伤肺腑。”高洋摇头:“他们能忍,我岂不能共?”话音刚落,忽见远处一队人影踉跄而来,为首者抱着个襁褓,跪倒在台前,泣不成声。
“都督……小人李五,村中孤户。妻因产难亡故,今寒冬难熬,孩儿啼哭不止,家中无薪无粮……求您救这孩子一命!”
高洋疾步下台,亲手接过襁褓。婴儿面色青紫,呼吸微弱,显然已近垂危。他立刻喝令:“速请医堂郎中来!调热汤暖室,取羊乳喂之!”又转身对随行官员厉声道:“北村竟有此等事,为何未报?民命司何在?登记簿册可曾入户核查?”那执事官面如土色,伏地请罪。
片刻后郎中赶到,施针用药,半炷香工夫,婴儿终于发出微弱哭声。高洋长舒一口气,将孩子交还其父,沉声道:“自即日起,凡新生婴孩,皆由乡里备案,官府供给三月口粮与炭火;产妇休养期内,免赋役,派专人巡诊。若有遗漏,以渎职论处。”
众人齐声应诺。那李五抱着复苏的孩子,叩首不止,泪洒雪地。围观百姓无不动容,有人低声啜泣,有人默默摘下帽子致礼。一名老农颤声说:“从前生孩子,怕的是活不下来;如今倒像是……有了指望。”
当晚,高洋召集民命司、仓曹、医堂诸官议事至三更。他亲自拟定《恒州育幼章程》,规定从接生到哺育、从防疫到启蒙,皆由官府统筹管理,并拨出专款设立“育孺仓”,储藏米糊、干酪、棉布等物,以备急用。又下令各村推举“慈母代表”,专司妇孺事务,直通民命司。薛孤延不解:“大人,新政已千头万绪,何须再添此细务?”高洋正色道:“治国如烹小鲜,不在鼎镬之大,而在火候之精。一个婴儿的性命,重过千军万马。若连新生儿都无法护佑,谈何民生?”
翌日清晨,风雪稍歇。高洋未及歇息,便亲赴城西织坊巡视。此处原为崔氏私产,新政推行后收归公有,改作官营织造局,专雇贫家妇女织布纺纱,按工计酬。他走入车间,只见数十名女子低头劳作,机杼之声不绝于耳。墙角一名少女忽然晕倒,众人慌忙扶起。
高洋上前查看,见她面色苍白,指尖冰凉。问知姓张,十七岁,家中三代寡居,靠此工钱度日,近日为赶年节订单,已连续劳作七日,昼夜不息。高洋默然良久,命人将其送医调理,随即召集管事训话:“工酬可增,不可夺命。自今日起,每日劳作不得超过六个时辰,夜不得加班,违者罚俸三月,重者罢职。”并立碑于坊门,刻写《女工十规》,明定休息、饮食、医疗、薪酬诸条,末书:“女子亦国民之本,血汗不容轻贱。”
回府途中,遇一孩童拦马献花??正是数月前赠他野菊的小女孩。她穿着新发的棉袄,脸颊红扑扑的,仰头笑道:“都督,娘说今年冬天不怕冷了,官府发了炭,还教我们砌暖炕。”高洋心头一热,俯身将她抱上马侧,柔声问:“你长大想做什么?”女孩不假思索:“我想当‘民命司’的姐姐,帮别人说话!”周围百姓哄笑,眼中却泛起泪光。
这一幕被画师悄悄记下,后来绘成《雪中抱童图》,张贴于各村公告栏,题曰:“为民者,当如是。”
然而暗流从未停歇。就在恒州渐现生机之际,晋阳再度传来异动。高欢病体反复,朝中权臣趁机蠢动。尚书左仆射孙腾虽已被贬,其党羽仍在暗中串联,散布谣言称“高洋僭制越礼,妄立私法,欲割据自立”。更有御史弹劾其“擅杀士族、结好边胡、蛊惑民心”,请求削其录尚书事之衔,召回京师“面询得失”。
杜丰得报,神色凝重:“大人,此乃构陷之辞,但若朝廷动摇,前功尽弃矣。”高洋冷笑:“他们怕的不是我杀人,是我让百姓识字、种地、议政。一个能读会算的农夫,比一万沉默的奴仆更让他们恐惧。”
他提笔修书致高欢,不辩解,不哀求,唯陈事实:列恒州新开屯田三百顷,收粮四万余石;建学堂十二所,入学孩童逾八百;民议堂通过惠民议案十七条,无一出自官府强令,皆由百姓公投决议;北疆互市开通三月,胡部归附者凡五千余口,愿为东魏守边。末尾写道:“儿所行者,非为权位,实为试一条路??一条庶民亦可抬头走路的路。若此为‘僭越’,则天下苍生皆当共僭;若此为‘悖逆’,则天理民心皆已先逆。”
书成,遣快马星夜送往晋阳。
与此同时,高洋并未坐等批复。他深知,唯有持续展示成效,才能击碎谣言。于是下令编纂《恒州新政实录》,图文并茂记录每一项变革:从第一口官井开凿,到第一场民选村正;从废除奴籍的告示,到盲童入学的场景。又命戏班排演新剧《破枷》,讲述一名农奴挣脱锁链、成为屯田队长的故事。演出那日,万人空巷,许多老人看着台上痛哭失声,喊道:“那是我爹一辈子没敢做的事啊!”
最令人震动的,是一场公开审判。纵火案最后一名从犯落网,竟是原恒州府衙文书赵德禄。此人出身寒门,曾受高洋提拔,却因贪贿被革职,怀恨在心,遂勾结王景文纵火泄愤。庭审当日,百姓齐聚民议堂外,屏息聆听。高洋亲自主审,证据确凿后,依法判处绞刑,同时宣布:“此人虽罪该万死,但其母年逾七旬,孤苦无依,官府将每月供给粟米一石,直至终老。非为宽恕罪人,只为不累无辜。”
判决既出,满场寂静。良久,爆发出雷鸣掌声。一位白发老者拄杖上前,深深作揖:“都督执法如山,仁心似海。老朽活七十岁,头一回见官府既讲理,又有情。”
此事传开,四方震动。洛阳学士裴子野叹曰:“昔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见‘小吏犯罪而母得养’,方知何谓王道。”
春正月初三,晋阳诏书终于抵达。高欢亲批:“览卿所奏,感慨良多。昔我少年时亦尝志在澄清天下,然困于世族牵制,步步退让。今观恒州气象,始知非世道无路,乃人心畏难。吾儿所行,合乎天心,顺乎民意,朕心甚慰。录尚书事之职,不动。”另赐金印紫绶,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位比宰辅。
消息传来,恒州全城燃灯三日。百姓自发集资,于城南立碑,上书“惠民之基”四个大字,落款为“恒州万民敬立”。高洋得知,连夜命人将碑文改为:“此基非一人所立,乃千万百姓共筑。”
立碑那日,突厥使者竟也远道而来。来者乃漠南部族首领之子阿史那云,携牛羊百头,言道:“闻都督仁德播于北疆,特来通好。愿与恒州互市,永为兄弟之邦。”高洋设宴款待,席间不谈兵戈,只论耕牧之法,赠其《垦荒指南》抄本,并允每年开放两季集市,公平交易盐铁布帛。
酒至半酣,阿史那云忽起身拔刀,众人惊骇,却见他割破掌心,滴血入酒,捧杯高呼:“自此以后,东魏若遭外敌,我突厥部愿出骑兵三千,助战死战!”高洋亦割指相和,一饮而尽。帐内将士无不热血沸腾。
事后杜丰忧道:“胡人多诈,此举恐有诈。”高洋望向北方辽阔草原,淡淡道:“信任如种树,总要先栽苗,才有望成林。他们若骗我一次,我信他们九次,第十次必得真心。”
春风将至,冰雪渐融。高洋率众巡查北原,只见新翻的土地如黑缎铺展,麦种已撒下大半。农夫们哼着新编的小调:“都督来了风雪退,犁头破土春先归。”几个孩童追逐着纸鸢奔跑,笑声清脆。
突然,一名驿卒飞马而来,脸色惨白:“启禀都督!晋阳急报……太夫人病危,丞相命您速归!”
高洋手中马鞭落地,久久不语。杜丰低声道:“大人,此去凶吉难料。高氏内部倾轧已久,若您离开恒州,旧党必乘虚而入。”高洋闭目良久,终于开口:“母亲生我养我,恩重如山。纵是龙潭虎穴,我也必须回去。”
临行前夜,他召集所有新政骨干于民议堂。烛火摇曳中,他逐一注视这些面孔??有曾为奴的农夫,有自学成才的匠人,有弃仕途投身乡里的年轻学子。他缓缓说道:“我不知还能不能回来。但我要告诉你们,恒州新政,不在某一个人,而在你们每一个人心中。制度已立,律法已行,只要你们坚持下去,哪怕我身死异地,这土地上的春天也不会消失。”
他取出一份密函封于铁匣,交予杜丰:“若我三月不归,或有变故传来,你便打开此匣,依计行事。其中所载,乃应对政变之策,包括军符印信、暗桩名单、以及……一道伪造的丞相手令。”众人震惊。高洋苦笑:“我不是圣人,只是凡夫。为了守住这片希望,我愿意背负任何污名。”
次日黎明,高洋轻装简从,仅带两名亲卫启程南下。城门外,百姓自发聚集数千,手持灯笼相送。那小女孩再次跑上前,塞给他一朵压干的野菊:“都督,等你回来时,我要给你看我写的字。”
马蹄踏碎晨霜,渐行渐远。高洋回首望去,恒州城楼沐浴在初升的朝阳中,宛如一座燃烧的灯塔。
他知道,这一去,或将面对父亲的责问、兄弟的猜忌、权臣的陷阱。但他更知道,身后那一片刚刚苏醒的土地,那一双双不肯低头的眼睛,已足以支撑他穿越一切黑暗。
冰层之下,暗流奔涌;春雷未响,万物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