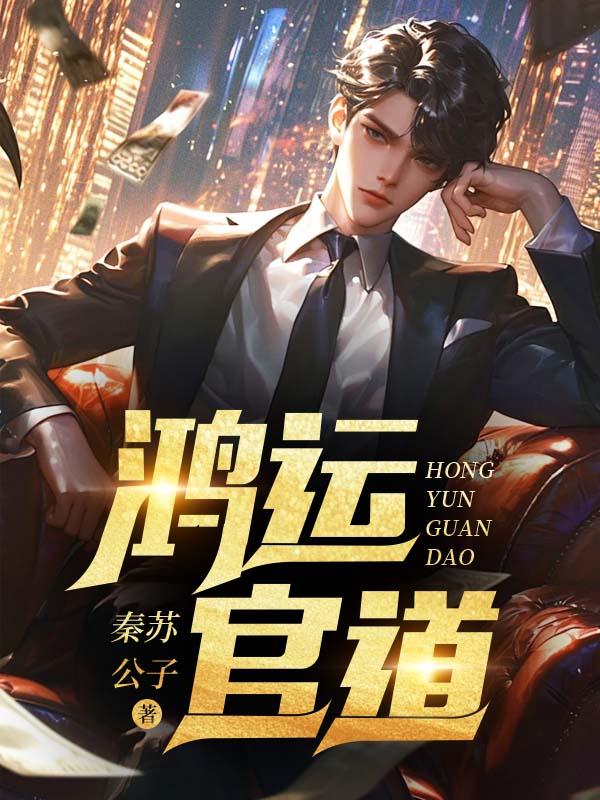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离婚后我的国医技能觉醒了 > 第919章 第一堂课(第2页)
第919章 第一堂课(第2页)
雷鸣般的掌声渐渐平息,教室里两百多双眼睛,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紧紧追随着讲台上那个年轻的身影。
陈阳手中那根细长的银针,在秋日斜照进来的阳光下,闪烁着内敛而坚定的寒芒。它不再仅仅是金属,仿佛成了连接古今、沟通师生的媒介。
“我们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阳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教室的每一个角落,带着一种奇特的安抚力量,让原本因拥挤和兴奋而有些躁动的空气沉淀下来。
“但于中医而言,这‘器’,不仅仅是这针、这药、这方。。。。。。更重要的,是驱使这‘器’的‘道’——那便是思维。”
陈阳放下银针,目光扫过前排一脸专注的墨浩博,掠过后面或好奇、或期待、或略带审视的面孔。
“《黄帝内经》开篇《上古天真论》,不讲如何治病,却大谈特谈上古之人的生活方式、精神境界。为什么?”
陈阳抛出了问题,没有立刻给出答案,而是留白,让思考在寂静中发酵。
几秒钟后,陈阳自问自答:“因为它告诉我们,理解疾病,首先要理解生命本身!理解生命如何与天地、四时、万物和谐共处,理解当这种和谐被打破时,失衡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中医思维的起点——整体观,天人相应。”
陈阳转身,在身后的白板上写下两个遒劲的大字:“象”与“数”。
“‘象’,是现象,是外在表现。病人发热、恶寒、汗出、脉浮……这些都是‘象’。”
陈阳解释道:“但中医不满足于看‘象’,更要通过‘象’去揣测内在的‘数’——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状态,阴阳寒热虚实的格局。这就是司外揣内。”
说着陈阳拿起讲台上一个普通的玻璃水杯,举了起来:“好比这个杯子。我们看到它外形完好也就是象,但若轻轻敲击,声音沉闷则是另一个象,我们就知道里面可能有裂痕,就会揣测其内部状态,即‘数’。诊断疾病,亦是此理。望闻问切,就是收集‘象’,再运用经典理论这把‘钥匙’,去解读内在的‘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这个简单又形象的比喻,瞬间让许多学生眼中亮起了“原来如此”的光芒。
枯燥的理论,在陈阳的口中好像也变得鲜活起来。
“那么,经典理论这把‘钥匙’怎么用?”
陈阳话锋一转:“死记硬背条文?生搬硬套方剂?那只会沦为‘方书医’、‘条文医’。我们要学的是其中的思维方法——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象’中,抓住核心病机;如何根据病机的动态变化,灵活调整策略。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髓,也是‘精要’所在!”
停顿了一下,陈阳的目光落回墨浩博身上:“墨浩博同学。”
墨浩博一个激灵,下意识地挺直腰板:“到!”
“我记得你前一阵,处理过一个风寒感冒初期的病人。”
陈阳问道:“当时病人主要症状是什么?你怎么考虑的?”
墨浩博没想到会被点名,还是在这么多人的课堂上,早知道就不坐这么靠前了。
“呃…病人恶寒重,发热轻,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苔薄白,脉浮紧,我…我当时考虑是风寒束表,肺卫失宣,准备用荆防败毒散加减。”
墨浩博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被提问,说话都有点结巴了。
“嗯,思路基本正确。”
陈阳点头肯定,墨浩博也松了口气,脸上露出喜色。
但陈阳紧接着追问:“但如果这个病人除了上述症状,还伴有明显的口干、咽痛,甚至舌尖有点红呢?荆防败毒散还能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