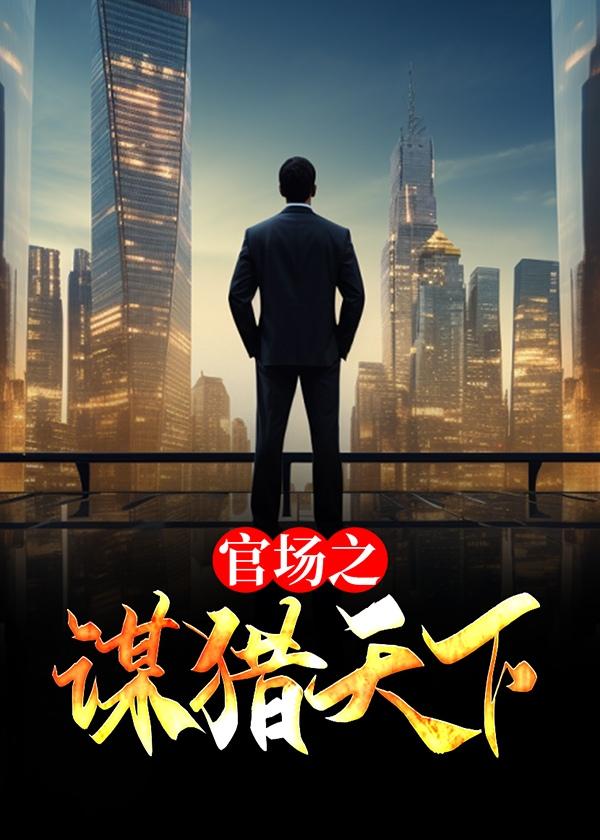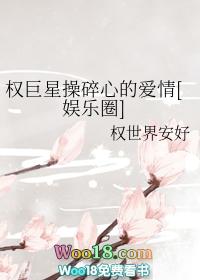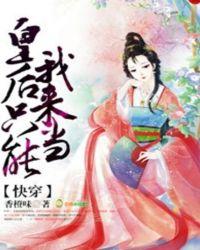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这个导演睚眦必报 > 第385章 阴阳大师被神仙姐姐续上了(第2页)
第385章 阴阳大师被神仙姐姐续上了(第2页)
这条微博再次引发热议,许多网友留言支持:
“导演,谢谢你没有选择逃避。”
“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来提醒我们不要麻木。”
“请继续拍下去,我们会一直关注。”
第八十四天,陈默接到一位公益组织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愿意协助他完成新片的实地调研,并提供拍摄期间的安全保障。
“我们知道这些孩子的生活很危险。”对方说,“但我们相信,您的镜头能让更多人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陈默点头:“谢谢你们的支持。但我必须强调,我不需要美化他们的苦难,我只需要真实地呈现。”
对方沉默片刻后回应:“我们理解。”
第八十五天,陈默前往一座偏远的城市垃圾场进行前期调研。这里没有正规管理,也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成百上千的拾荒者在这里日复一日地翻找废品。
他带着摄像机,悄悄记录下一个个真实的瞬间:一个男孩蹲在地上捡矿泉水瓶,手上的冻疮已经溃烂;一个小女孩抱着一本破旧的识字书,对着阳光一页页地念;还有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用手中的废纸板搭建起一个临时的“教室”。
他站在远处,默默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
他知道,自己即将拍下的,不只是电影,而是一份控诉。
一份关于遗忘与忽视的控诉。
第八十六天,陈默回到城市,开始撰写剧本。他不想用太多台词,也不想加入过多戏剧化的冲突。他只希望,观众能通过画面,感受到这些孩子的存在。
他在剧本开头写下一句话: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这是我们的世界。”
第八十七天,李文澜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红手套》在柏林电影节展映后反响热烈,多家国际媒体给予了高度评价。
其中一家德国报纸写道:
>“陈默的镜头冷峻而温柔,他不煽情,也不控诉,但他让每一个观众都无法移开视线。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见证之影’。”
另一家法国杂志则评论: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陈默的作品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表面的繁华,直指社会最深处的伤口。”
陈默看完这些评论,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将这些报道截图保存下来,发给了当初资助他第一部电影的那位基金会负责人。
他在信息中写道:
>“感谢你们的信任。
>我会继续拍下去,哪怕只有一束光,我也要让它照亮黑暗。”
第八十八天,陈默收到一封来自某知名电影节组委会的邮件,邀请他担任主竞赛单元评审团成员之一。
他看完邮件,轻轻一笑。
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主流排斥的独立导演了。
但他也清楚,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