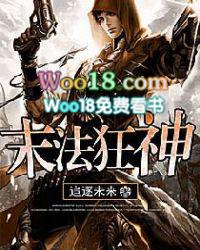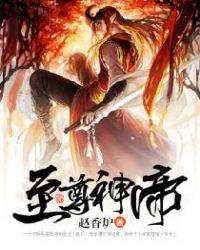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大唐协律郎 > 0260 刺史雅兴礼佛虔诚(第1页)
0260 刺史雅兴礼佛虔诚(第1页)
汴州的相国寺历史悠久,始建于北齐年间,据说这寺址乃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魏国信陵君的宅邸。
寺庙最初名为建国寺,初唐时毁于战火,后来又经重建。唐睿宗李旦以相王而继大统,于是便诏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并出。。。
张岱回到驿馆时,已是黄昏。他坐在案前,提笔沉思片刻,终于在纸上落下一行字:“茶叶之利,不在一时之得,而在长久之势。”
这并非他一时兴起的投机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布局。茶叶虽非盐铁那样的国家命脉,却因其消费群体广泛、流通渠道灵活、利润空间可观而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更关键的是,它尚未被朝廷列入重税或专营之列,正适合用来作为突破口。
“若能在龙门、北邙等地包山种茶,再借漕运之力输送至魏州、汴州乃至河湟朔方,既能吸纳大量流民劳力,又可借此调动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张岱心中已有全盘构想,“如此一来,便可绕开官府直接干预,同时又能为地方财政开源。”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掌握足够的土地和资金支持。而这,也正是他将目光投向汴州的原因。
源复虽然能力平庸,但在汴州经营多年,手中仍握有不少资源。更重要的是,他是源乾曜之子,背后站着一个宰相家族。只要能说服他加入此事,便可借助其名望与人脉迅速打开局面。
想到这里,张岱便取出纸笔,开始撰写一封致源复的长信。
他在信中详细列举了茶叶产业的前景,包括种植成本、加工流程、运输方式、市场需求等,并附上自己在魏州市场考察所得的数据作为佐证。最后,他还特别强调:“此业若成,不仅可为州府创收,亦可助宇文融兄在魏州立功,进而为我等日后仕途铺路。”
写罢,他将信封好,命人快马加急送往汴州。
---
与此同时,魏州刺史府内,宇文融正翻阅着几份新到的奏报,眉头紧锁。
“张岱果然不是寻常人物。”他低声自语,“短短数日,便已察觉茶叶之利,并迅速着手布局。”
他当然也明白,张岱此举绝不仅仅是为了替魏州谋利,更是为了借此掌控一部分独立于官府之外的经济资源。这种做法虽然风险不小,但如果成功,确实能为他日后重返朝堂增添几分筹码。
“问题是……源复会答应吗?”宇文融喃喃道。
他知道源复性格优柔寡断,遇事往往瞻前顾后,若让他主导此事,恐怕只会拖慢进度。然而,若由自己强行插手汴州事务,又难免引起源乾曜的不满,甚至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
思忖良久,他最终决定采取折中之策??将张岱的计划转达给源复,同时附上一封亲笔信,措辞极为委婉:“此计可行与否,全在你一念之间。”
他没有明说自己的立场,只希望源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
汴州城内,源复收到信件已是三日后。
他坐在书房中,反复阅读张岱所附的那份详尽报告,神色复杂。
“茶叶……”他低声重复了一遍,随即陷入沉思。
他并不怀疑张岱的能力,更清楚此人一向眼光独到,行事果决。若真要在茶叶上做文章,未必不能成事。可问题在于,自己是否愿意参与其中?
“若我答应,便是彻底站在宇文融一边,与父亲的关系也将更加微妙。”源复心中挣扎,“可若拒绝,恐怕连这最后一丝机会都要失去。”
他抬头看向窗外,月色如水,思绪万千。
“罢了,先看看再说。”
于是,次日清晨,他便召集了几位亲信幕僚,开始着手调查汴州境内是否有适合种植茶叶的山地,以及本地富户对投资茶叶生意的态度。
一场围绕茶叶的博弈,悄然拉开序幕。
---
而在长安,源乾曜也在密切关注着魏州与汴州的一举一动。
“宇文融这是想借茶叶翻身?”他轻叹一声,将手中的奏报放下。
作为宰相,他自然清楚朝廷对地方经济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尤其是一些新兴行业,如茶叶、香料、药材等,往往游离于赋税体系之外,成为某些官员私囊的重要来源。
“若宇文融真能在魏州做出成绩,倒也是一件好事。”源乾曜心想,“只是,他会不会太过激进?”
他并不反对改革,但前提是不能触动根本。而宇文融的做法,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敏感地带。
“看来,是时候该提醒一下他们了。”源乾曜拿起朱笔,在一份奏折上批注道:“凡新业之兴,须慎之又慎,务求稳中求进。”
这道旨意很快便传至魏州与汴州,表面上是鼓励地方发展经济,实则也是一种警告。
---
张岱对此毫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