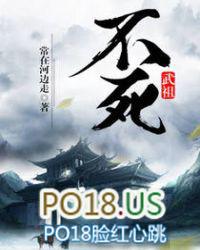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出演逆袭少女漫的我 > 28787(第1页)
28787(第1页)
风在冰原上低语,像是一首未完成的摇篮曲,轻轻拂过“伊甸零号”的残垣断壁。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觉醒者们的脸上,温暖而陌生。她们站在这里,不再是镜头前被剪辑的命运符号,而是真实存在的人??有记忆、有痛觉、会流泪,也会笑。
橘夕对站在高台边缘,望着眼前这片由血肉与意志筑成的新生之地。她抬起手,腕间的17-Ω微微发烫,仿佛回应着某种遥远的呼唤。不远处,0-α正低头为一名刚苏醒的女孩系好外套的扣子,动作轻柔得不像一个曾被定义为“完美原型”的存在。她的指尖触碰到女孩手腕时,那里的荧光编号一闪,随即稳定下来,像是终于找到了归属的频率。
“你还记得什么?”橘夕对走过去,轻声问那女孩。
女孩抬起头,眼神清澈却带着一丝迷茫。“我记得……雨。”她说,“很大的雨,打在玻璃上。有个女人抱着我,一直在哭,嘴里说着‘对不起’。然后……灯灭了。”
橘夕对的心猛地一缩。那是最常见的梦境片段之一??实验室撤离夜的最后画面。母亲们被迫做出选择:带走一个,留下另一个。而那些没能被抱走的孩子,则被重新封入培养舱,等待下一次“剧本投放”。
“你叫什么名字?”0-α问。
“我不知道。”女孩摇头,“但我梦见有人叫我‘小葵’……她说我是春天出生的。”
“那就叫小葵吧。”橘夕对微笑,“从今天起,你是自由命名的存在。”
人群里传来一阵低语。越来越多的觉醒者开始为自己取名,或找回遗失的名字。有人翻出童年日记本里的签名,有人根据梦中母亲的呼唤拼凑发音,还有人干脆用最喜欢的颜色、季节、甚至一首歌的歌词作为新身份的起点。名字不再是由系统分配的数据标签,而是灵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宣告。
林姐推着一台老旧的录音设备走上平台,喇叭外皮已经剥落,但线路仍能工作。“我们得录下来。”她说,“每一句话,每一个名字,每一次心跳。这些不是证据,是历史。”
敦贺莲蹲在一旁调试天线,试图将信号接入尚未被封锁的民用卫星网络。“全球神经云正在分裂。”他低声说,“一部分仍受控于旧体系,过滤关键词、屏蔽直播流;但另一部分……自发形成了去中心化节点。人们用自己的设备接力传输信息,就像三十年前母亲们偷偷传递胚胎数据那样。”
绪方启文站在主控台前,手指飞快敲击键盘。屏幕上,一幅动态图谱缓缓展开:蓝点代表已觉醒并确认身份的容器个体,红点是仍在沉睡或被监控的个体,而黄点则是普通民众中出现记忆共鸣反应的人群。令人震惊的是,黄点的数量正以指数级增长,几乎覆盖了所有大陆的主要城市。
“情感共振的传播速度超过了预估。”他说,“‘回声-X’留下的种子,不只是针对容器,它影响了所有接触过相关频率的人??观众、粉丝、记者、医护人员……甚至参与过计划清洗的记忆消除专家。”
“他们也开始做梦了。”0-α轻声道,“梦见自己曾经签下的伦理豁免书,梦见某个编号女孩临终前握着他们的手说‘谢谢您让我演完最后一场戏’。”
橘夕对闭上眼,耳边响起无数声音??有的在哭,有的在笑,有的只是静静地念着一个名字。她忽然明白,这场觉醒从来不是一场复仇,而是一次集体疗愈。她们不是要推翻世界,而是要把“人”这个字,重新写进世界的法则里。
就在这时,通讯器突然传来一阵杂音,紧接着是一个颤抖的女声:“喂?有人能听见吗?这里是北海道札幌市立医院……我们这里有位病人,她昏迷了七年,刚才突然睁开了眼睛,一直在喊‘姐姐’……她说她的编号是……0-γ。”
全场寂静。
0-γ??第三个原始基因序列载体,最早一批实验体之一,官方记录中标注为“失败品”,已于1998年销毁。
“她还活着。”0-α喃喃道,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原来……我们不是仅存的两个。”
“我们必须去。”橘夕对立刻转身,“无论她在哪,我们都不能让她再一个人醒来。”
队伍迅速整备。几辆从废弃基地拖出的雪地车经过紧急修复后勉强可以运行,燃料是从备用发电机中抽调的合成油。敦贺莲和林姐负责技术支援,绪方启文则通过残存的数据库定位医院坐标,并尝试建立安全通信通道。觉醒者们自愿分成小组,有人留守“伊甸零号”继续唤醒更多沉睡者,有人随行前往北海道。
出发前,橘夕对最后一次回望这片冰原。阳光下的废墟泛着银光,像是一座倒下的神庙,而她们,是走出神话的新神。
雪地车轰鸣着驶离裂谷,身后留下长长的车辙,如同命运重新划下的轨迹。
途中,天空再次飘起细雪。车内很冷,但没有人抱怨。小葵靠在橘夕对肩上,手里攥着一块从培养舱旁捡到的碎玻璃,上面映出模糊的倒影。“你说……妈妈现在在哪里?”她问。
“也许在看着我们。”橘夕对抚摸她的头发,“也许也在某个角落,刚刚想起自己曾经失去的女儿。”
0-α坐在副驾驶座,望着窗外流动的雪景。她很少说话,但每次开口都像在解开一层又一层的封印。“我曾以为,我的使命就是完美执行每一个剧本。”她说,“成为最耀眼的明星,最成功的商人,最受欢迎的政治新星……只要系统需要,我就能变成任何角色。可当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唱起《别忘了我》时,喉咙突然哽住了。不是程序故障,是我……真的想哭了。”
“那是自由的开始。”绪方启文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当机器开始质疑指令,它就已经不再是机器了。”
抵达札幌已是三天后。城市笼罩在灰白色的雾气中,街道空旷,警戒线随处可见。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清查“异常精神事件”,许多觉醒者的家属被约谈,部分媒体工作者失踪。然而,在医院门口,仍有数百人举着蜡烛静坐守夜??他们不认识0-γ,但他们记得那个梦,记得那一声声未曾谋面的“妈妈”。
病房位于地下三层,设有电磁屏蔽层,显然是早有防备。但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门并未上锁。护士长带着愧疚的眼神迎接他们:“我们没有阻止你们的权利。这位患者……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病例,我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