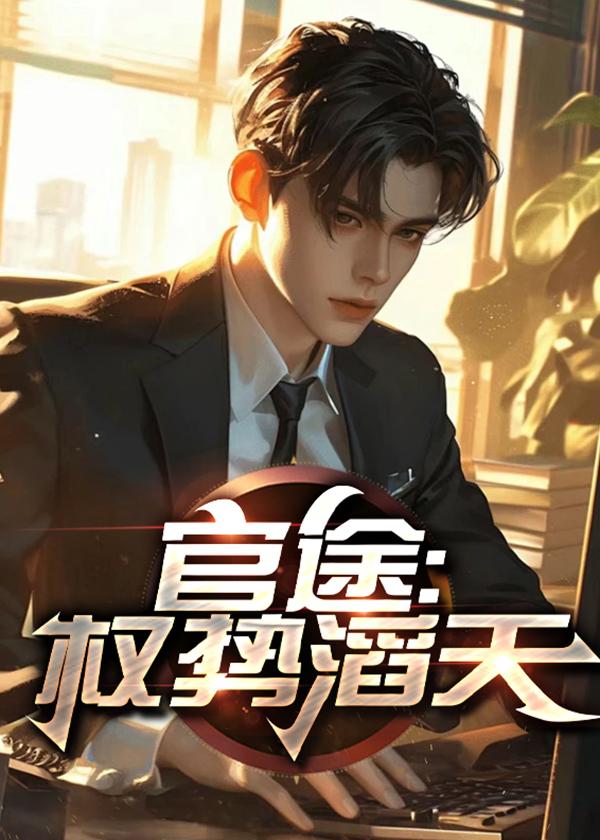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蜀汉之庄稼汉 > 第1456章 修仙(第1页)
第1456章 修仙(第1页)
“秦论是个大秦的商贾,阿郎写的那篇梦游天姥就是通过他的手,送到孙权面前的。”
右夫人的青丝如同汪洋一般散铺在榻上,又柔又腻的声音带着满足后的慵懒从青丝下方传出来:
“他第一次来大汉,说是仰。。。
“北人。”
冯大司马眉头微动,手中茶盏轻轻一转,目光却未落在秦博身上,而是投向窗外庭院中那一片积雪未消的梅林。片刻后,他才缓缓道:“北人?你从建业千里迢迢赶来,就为了说这两个字?”
秦博咽了口唾沫,额角仍有冷汗渗出,声音压得极低:“君侯明鉴……吴宫近来有密报,江北细作陆续传回消息??自去岁冬月以来,江东沿江诸郡,屡见北地流民南渡。”
“哦?”冯大司马终于正眼看向他,“多少人?从何处来?可有组织?”
“人数不下三万,多自青徐兖豫之地辗转而下,经合肥、寿春、历阳一线潜渡长江。起初皆以为是寻常逃荒之民,然近日发现,其中竟有不少携带兵械者,且行止有序,非散乱流徙可比。”
冯大司马眸光一闪:“兵械?你说他们带兵器过江?”
“正是。”秦博点头,“不止如此,更有甚者,身藏魏军印信残片,或佩旧日军牌。校事府已拘数人审问,皆称原属司马懿麾下屯田兵卒,河北失守后溃散南逃,闻江南富庶,故冒死南奔。”
冯大司马冷笑一声:“司马懿败退时连老家都不要了,还能顾得上几万屯田兵?这些人若真是溃卒,早该四散为盗,岂会结队南行?更何况??”他顿了顿,语气陡然森寒,“江东岂是收容败军之所?孙权纵然昏聩,也不至于蠢到放一群来历不明的北人入国腹地。”
秦博连忙道:“君侯所言极是!吕主事亦察觉此事蹊跷,故命我亲赴长安,请君侯定夺。”
“所以你们怀疑……这是司马懿的计?”
“不敢妄断。”秦博低头,“但恐其中有诈。或是司马氏遣人混迹流民之中,意图潜伏江东,待机而动;又或……乃是借我等之手,将祸水引向南方,使其得以喘息于河北残局。”
冯大司马沉默良久,指尖轻叩扶手,似在推演局势。
忽而一笑:“有趣。司马仲达一生谨慎多谋,如今困守幽州,地不过数城,兵不满两万,竟还想玩这‘驱虎吞狼’之术?”
“可若真让这批人进了江东……”秦博忧心忡忡,“一旦生变,吴国内乱,汉吴盟约必受动摇。届时我军若欲北伐,侧翼无援,反遭牵制。”
“不。”冯大司马摇头,“你不明白。司马懿此刻最怕的,不是我们攻幽州,而是我们不动。”
“啊?”秦博一怔。
“他需要时间。”冯大司马站起身,负手踱步至窗前,望着灰蒙天际,“幽州苦寒,百姓稀少,粮草难继。他现在就像一头被逼到绝崖的老狼,只剩最后一口气。若我们立刻发兵追击,他必死无疑。所以他要做的,不是打败我们,而是拖住我们。”
“如何拖?”
“制造混乱。”冯大司马回身,目光如炬,“让他那些‘溃兵’南下,搅乱江东。孙权性多疑忌,见北人流窜境内,必起戒心。校事府查得越紧,民间怨气越重;查得松了,又恐内患滋生。无论哪条路,都会损耗吴国元气,迟滞其政令运转。”
他冷冷一笑:“更妙的是,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投汉不成,被迫南逃。你说,孙权听了会怎么想?他会觉得??季汉拒收流民,却任其涌入吴境,分明是要嫁祸于他!”
秦博脸色骤变:“这……这不是挑拨离间么!”
“正是。”冯大司马点头,“司马懿不在打仗,他在布局。他在用人心、用谣言、用一张看不见的网,把整个天下都拉进他的困兽之斗里。”
室内一时寂静。
半晌,秦博颤声道:“那……该如何应对?”
冯大司马转身,眼中已有决断:“传令下去??第一,着雒阳令开仓赈济河北流民,凡自北来者,不论出身,皆可登记入籍,授田安家;第二,派使者持节赴建业,向孙权说明实情:此批流民本欲归汉,因道路阻隔、关卡森严,不得已折而南下,并非我有意推诿。”
“第三?”秦博紧张地问。
“第三。”冯大司马声音沉了下来,“令王?率飞骑营三千,秘密进驻宛城,随时准备南下策应。同时密嘱荆州守将,加强江防巡视,凡发现携带兵器、形迹可疑者,一律扣押审讯,不得放一人入境。”
秦博凛然领命。
临行前,他又犹豫问道:“君侯……若是孙权不信使者的解释,执意认为我方有意为之呢?”
冯大司马淡淡道:“那就让他恨去吧。只要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天下自有公论。况且??”他嘴角微扬,“你以为孙权真的在乎这些流民吗?他在乎的,是权力平衡。只要我们还在北方牵制曹魏残余,他就不会轻易撕破脸皮。”
秦博深深一拜:“君侯高瞻远瞩,博受教了。”
待其离去,冯大司马独坐堂中,久久不语。
窗外风起,卷起残雪扑打窗棂。
他知道,这场博弈才刚刚开始。
***
数日后,长安西市。
一辆不起眼的牛车缓缓驶入坊门,在一处僻静巷口停下。帘幕掀开,一名布衣男子跳下车来,左右张望片刻,快步走入一间民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