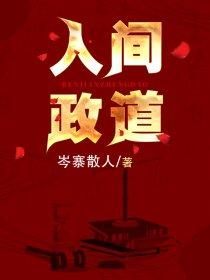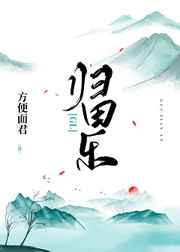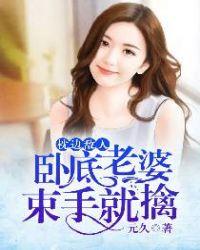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尘河酒 > 夜半客(第1页)
夜半客(第1页)
“你是不是在找那个皇太女。”阿兰忽然说。
“什么皇太女!”易涟清一瞬间就知道他说的是谁,可是阿兰怎么会知道,又是谁告诉他那是皇太女的?!
阿兰无所谓地耸耸肩膀:“她自己说的,她来找过你,不过那时候你已经出发去京城了。”
那个女孩不是在易家的严密监控之下吗?为什么还能跑出来找她,甚至在很久之前就有心找到她?
她既然自称皇太女,便是有心参与皇位之争,不像是个软弱的性子。易涟清一边一头雾水地让人翻找章德太子留下的记录,一边催促连华帮助陆端寻找失踪的皇太女。
章德太子生在宫中,长在宫中,死在宫中。人生短暂的二十年中甚至鲜少走出宫城,更遑论像光诚帝那样四方巡查,冬狩春猎。
浩如烟海的卷佚组成了章德太子的一生,易涟清不断翻看着,和自己印象中的那个很温和的兄长逐渐结合在一起。
太子十六岁迎娶正妃,琴瑟和鸣,情投意合,太子妃出走宫禁,未尝没有伤心欲绝的因素在其中。
章德太子在她第一日入学时等在门外,众目睽睽之下牵起她的手,从连华手中拿过她在课堂上写的那篇策论,就站在弘文馆的门前仔仔细细读了一遍。
太子在学生们中间很有威望,因为曾经在弘文馆读书,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先生,几个放了学的小皇子叽叽喳喳地围在他身边,却不敢出声打扰。
等到太子看完,对她的文章大加赞赏。太子人虽然和蔼,治学却很严谨,不少孩子都害怕在弘文馆中被他点到名字,这通常意味着要去背书或者改文章了。
听到太子赞赏,那些原本因为她是女孩而轻视的目光改变了,好奇、探究地看着她。太子便用她的策论,一字一句讲解。
时间过去太久,具体写了什么东西已经忘记了,不过绝不像太子口中所说的那样,结构精妙意蕴深长。
其实没有太子的帮助,易涟清在弘文馆中也不会过得很艰难,可是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因为钟阁老的孙女在弘文馆中上学是唯一的女孩,便要想法帮她。
章德太子清俊、消瘦,穿着一身平平无奇的文士袍,袖子里是淡淡的皂角味道和栀子花香气,因为太子妃名字中有个栀字。
如果生在平凡人家,他一定是个教书先生,带着乡村中的一群野猴子读书,不管他们怎么调皮都不生气,可是学问又管得很严格,只要稍微冷脸,野猴子们只好重新变成人,忍着眼泪抽抽嗒嗒地在他面前排队背书。
可惜生在帝王家,越是娇养,越是短命。
他有过一次中毒的记录,不过并非有人蓄意谋害,而是个巧合。太子妃亲自下厨做了些饭食给他,宫人没注意,晚上准备了相冲的食物,因此中毒。
粗心的宫人被赶出宫外,太子妃再也没有下过厨房,此事简单地结束了。
可是这两样食物并不是常见的相冲的东西,似乎章德太子刚刚显现症状时,太医并没有反应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开了一副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子,吃过一次之后忽然变了方向。
难道是找到了相似的症状?事发时已经是半夜,就算到宫外去找郎中,也不可能正正好好找到一个处理过相似问题的郎中。
而且第一幅药才刚刚吃下去,没道理还没显现出效果就直接出宫。易涟清飞快地向前翻着,连翻过七八本,目光一凝。
二十年前的光诚帝,出现过一模一样的症状。可是究竟如何发生的,又讲述得语焉不详。
没办法,只好又去找当天的起居注,妄图从中找到一点什么线索。
不知是运气好还是此事实在过于蹊跷,春秋笔法无法掩盖,易涟清从中只读出来微妙的一句话。光诚帝中毒是因为易则铮。
那一日伴驾的不是什么皇后或者贵妃,而是名不见经传的易家之子易则铮。膳房没有记录,因为让光诚帝中毒的那顿饭是易则铮做的。
光诚帝中毒醒来后,稍微康复一些,让易则铮觐见,不知道说了什么,大怒,将他打入天牢。进了天牢的人往往只有死路一条,可是过了没多久,光诚帝想开了似的,又把人放了出来。
一切都微妙得难以言喻。光诚帝不是那种因为下人无意间做了相冲的食物就大发雷霆要了下人性命的人。他既然将易则铮打入天牢,就是知道他是存心的。
这事本来就严重,加上弑君的罪名,是要诛九族的。本该诛九族的易则铮被光诚帝莫名其妙地消了气以后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