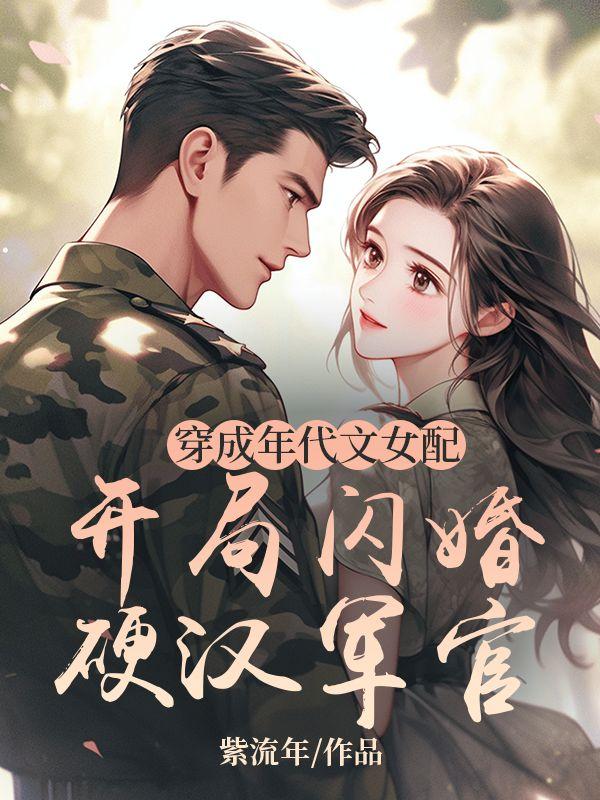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尘河酒 > 鬓边(第2页)
鬓边(第2页)
“别叫什么殿下,名不正言不顺的。”陈阳说完之后,转过头看着院子里的那棵树。她幼时跟在母亲身边,母亲在梳妆打扮齐整之后,就坐在那里,一日复一日地望着窗户外面。
她曾经疑惑过,凑到母亲身边去,想知道母亲到底在看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一棵树、一树花、一只鸟。她不知道那些有什么好看的,直到她坐在这里,穿金带银,衣着华丽。
她甚至比不上母亲的处境。她身边还有太子,下了朝,太子会短暂地陪伴她一段时间。每到这时,母亲像是画中人从纸上走出来,忽然鲜活,可是等到太子离开,又重新变回纸人。
太子妃是个毫无错处的大家闺秀,出身高贵,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与太子门当户对,婚后打理内宅事务从未出过差错。唯一一次叛逆,就是带着她离开京城。
陈阳没有问过她,当初带着她离开,究竟是因为觉得她是女子,还是想要带着她远离这些争端。她不敢问,害怕听见母亲对自己的评判。
但是当易家的人找上门来,母亲将那些人关在门外,问她愿不愿意去京城。她似乎觉得她还不明白去京城究竟意味着什么,张口想要对她说明,可是看见那双坚定清澈的眼睛的时候,母亲就没有再说话了。
“你送到我身边的时候才那么一点大,”母亲说,“明明一点都不想认我做母亲,可是他们要你叫,你就乖乖地叫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和我不一样,”母亲摸了摸她的头,母亲从来都是母亲的样子,温柔慈爱,可是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陈阳始终没有看清。母亲说,“你比我有出息得多。”
可是在易家,作易家的牌匾、易家的旗帜、易家绑架来用以谋权篡位的幌子,她迷茫。母亲说她有出息,可是她作易家的傀儡,将来作大梁的傀儡。
她不甘心。她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人,她看见易家人的面孔和神情,就知道他们想要做什么。
她没有被他们信任,但他们也没有重视她没有防备她,易家人眼中,他们已经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没想到她宁可鱼死网破,也要把账本和罪证送到陆端手上去。
“殿下,”有人在门外敲了敲,弯着腰,很是谦恭,“众人都到齐了,等着陛下赏脸。”
镜子里的人面无表情,口脂鲜艳,红得像血,她从袖子里取出帕子,擦掉了那一抹红色。
她在婢女的指引下走进大厅,丝竹一刻也没有停歇,熙熙攘攘的人群只安静一瞬。她知道他们的安静是给她肖似生母的那张脸。
她不知道母亲姓甚名谁,至少听人说有一张相当美丽的面孔,才会被父亲收入宫中。
他们惊叹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她的容貌美丽,甚至不是为了她与父亲相似的眉眼。遗孤、皇太女、未来的新帝,都只是他们手中的玩意而已。
陈阳没有表现出不悦,她的表情甚至纹丝不动,对着众人微微一笑。目光扫到的人,都已经在灭亡的边缘,还浑然不觉地吃喝着。
他们窃窃私语:“这就是皇太女?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一个歌伶舞姬样的人物。”
他们用狎昵的眼神在易大人和她的身上来回流转,她不用猜都知道他们会想些什么。但是无所谓了。
陆端的刀已经高悬在他们头上,等到他们死尽,这把刀再回到陆端的头上。
她不确定要不要杀了陆端,她曾经和母亲讨论过这个人,母亲轻轻地笑了一下,低下头借着缝补她磨破的护膝:“是个难得的情种,只是可惜易涟清到西突厥去了。”
易涟清。
她听着这个名字长大。她母亲是易涟清的大嫂,而不是谁的太子妃谁的皇后,易涟清在弘文馆同太子论政时,母亲带着糕点去送给她。
那时母亲一直在盼望着自己的孩子,无处安放的母爱就寄托在易涟清身上。她搂着那个小女孩说希望自己将来也能生出一个这样聪明这样可爱的孩子。
易涟清说一定会的,阿姐人这样好,老天爷一定不舍派个混世魔王来闹你。
母亲回忆易涟清的时候,目光悠远,她知道母亲不仅仅是在回忆易涟清,更是回忆父亲和她最好的那段时光。
可是她仍然有些失落,母亲似乎看出了她的失落,于是很少提及过去的那段时光。其实不必的,她想对母亲说,易涟清是个遥远的幻影,当你为了我避而不谈的时候,我已经不会失落了。可是她最终没说,有那么多人都在回忆易涟清。
临走前,她终于鼓起勇气问母亲:如今的我,能让你觉得堪做你的女儿吗?
母亲看着她微笑: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一样的人,也早就知道这一天。不要再想着她了,京城将来是你的天地。
她辞别了母亲,走到这个污糟的朝堂中来,用利剑对准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