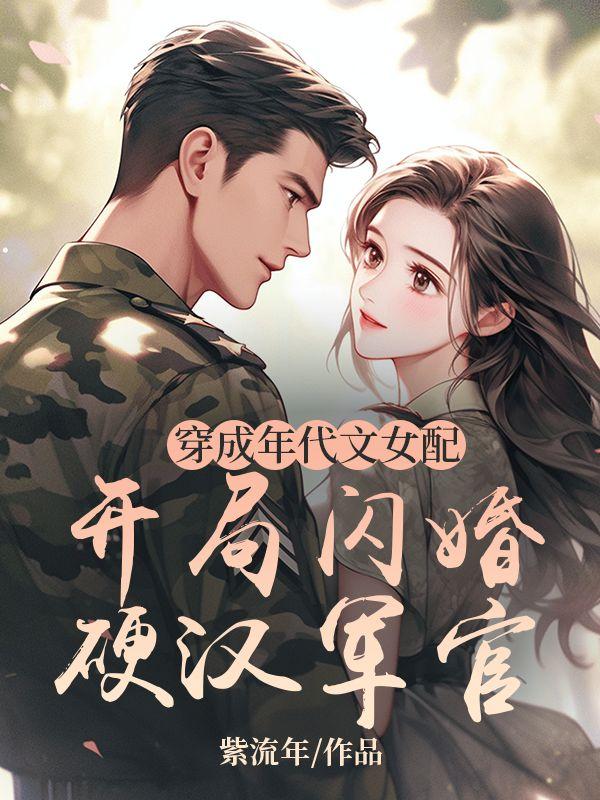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流浪在中世纪做奴隶主 > 第436章 除夕将至(第1页)
第436章 除夕将至(第1页)
一月底的托尔托萨,卡莫村在冬日的寒风中喧嚣而热闹,地中海的咸湿气息混杂着柴火与烤饼的香气,飘荡在石墙与泥瓦房之间。夏历除夕将至,归乡的沙陀人拖着吱吱作响的木车,载着布匹、干果和香料,陆陆续续回到村子。村口大道上,孩子们追逐嬉戏,笑声清脆;井边,妇人们汲水闲聊,分享除夕祭祖的准备。
村子中央的广场上,萧书韵和扎伊纳布正忙得热火朝天。萧书韵一袭青布长衫,袖子高高挽起,手持一把粗糙的苇帚,卖力地清扫着院落里的落叶和尘土。她的脸颊被寒风吹得微红,额头上却渗出细密的汗珠,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震旦小调,曲调悠扬却带着一丝乡愁。扎伊纳布则裹着深色头巾,麻利地擦拭着木窗框,嘴里不时冒出几句天方教的祷词。她们偶尔停下来对视一眼,笑着抱怨这房子怎么总也打扫不完,却又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不远处,观音奴的身影一闪而过,宛如幽灵。她披着一件破旧的灰色斗篷,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斗篷下摆被杂草勾得乱七八糟,沾着湿泥与未干的血斑,看不出是人是鬼。她手里提着一把锄头和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袋口缝得死紧,像是包着什么脉动的东西,偶尔传出几下细微却令人不安的窸窣声。
观音奴行色匆匆,像是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驱赶着,穿过村里蜿蜒狭窄的羊肠小道。每当有村民路过,她便迅低头,脚步一顿,贴墙而行,仿佛阴影本身长了双脚。几个孩子藏在屋后悄悄张望,窃窃私语:“她的斗篷里藏着蛇呢,我昨晚听见嘶嘶声!”另一个则摇头:“不对,我看她从坟地那边回来,说不定在刨死人骨头炼黑魔法!”
自从来到托尔托萨,观音奴总在黄昏时分神神秘秘地回村,身上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气味——青草、湿苔、老木、烂泥,还有点淡淡的铁锈味,有人说像山里刚挖出来的棺材板子,有人则干脆形容是“风吹半月死蛇烂”,恶心得直皱眉。观音奴每次都在附近那片树林里钻进钻出,一头扎进去几个时辰,有时甚至天黑了还不见人影。
起初大家以为观音奴在找什么药草,后来见她每次都是空手而归,却眼神亮、嘴角带笑,便有人嘀咕她是不是被山鬼迷了魂魄,日日寻宝寻得疯魔。观音奴嘴里倒是说得振振有词,什么“沙陀人的宝藏”、“沙陀人祖上留下的金子”等神神叨叨的话,但除了观音奴自己,没人信这胡扯。李漓听观音奴说这些只当耳边风,从未当真——他压根不记得自家哪代祖宗还有闲情埋金子玩传说。
萧书韵站在门口,看着她远去的背影,眼角微微跳了跳,眉头越皱越紧,低声对扎伊纳布嘀咕:“这丫头,最近越古怪了,怕不是又在捣鼓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扎伊纳布正倚着门框磨指甲,听了这话撇了撇嘴,笑得满不在乎:“她这人脑子有毛病,理她干嘛。再这样下去,别说宝藏,她怕是先要把自己埋进去了。”
萧书韵轻轻哼了一声,却没说话,只是目光仍停在那片被黄昏吞噬的小树林方向,若有所思。
与此同时,约安娜和比奥兰特的“实验室”——一间改装过的谷仓——里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谷仓的木门半掩,里面飘出阵阵橄榄油和蜂蜡的香气,夹杂着某种花草的清苦味道。约安娜盘腿坐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堆陶罐和木杵,专注地捣碎干枯的草药,嘴里念叨着配方的比例。比奥兰特则站在一旁,拿着一块粗布小心翼翼地搅拌着一锅正在加热的乳膏,脸上满是兴奋:“再加点薰衣草油,香味得更柔和些,天方教的贵妇们最爱这个!”谷仓外,埃尔雅娜和伊纳娅已经等得不耐烦,催促她们赶紧拿出样品——十字教世界的贵族与骑士夫人们和天方教世界的哈里后宫,都在等着这神奇的防晒膏来保护她们娇嫩的皮肤。
村子另一头,朗希尔德的家门口却是一片祥和。她斜靠在铺着羊毛毯的木床上,啃着一块刚烤好的大麦饼,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她的肚子微微隆起,裹在宽松的亚麻裙里,整个人散着母性的光辉。萨赫拉和几个邻居妇人围在她身旁,七嘴八舌地传授着保胎的“秘方”:喝羊奶、吃枣子、千万别碰冷水。朗希尔德只是笑着点头,懒洋洋地伸了个腰,嘴里嘀咕:“吃吃睡睡,真是最好的日子。”她身旁的小桌上,摆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和一碟蜜饯,香气扑鼻,引得窗外的野猫都探头探脑。
然而,这份节日的喜庆却被村东侧的一片混乱喧嚣盖过——六百多亚美尼亚流民的到来,让卡莫村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忙碌与挑战。村东的空地上,临时搭建的帐篷和木棚密密麻麻,宛如一片杂乱的蜂巢。五百多亚美尼亚人,拖家带口,衣衫褴褛,挤在这片新开辟的营地里。他们被十字军以“异端”之名从耶路撒冷驱逐,北上返乡的路上耗尽了粮食与气力,形容憔悴,眼神中满是疲惫与不安。空气中弥漫着烤焦的谷物、汗水和牲畜粪便的味道,哭声、争吵声与孩子的尖叫交织在一起。几个妇人围着火堆,用仅剩的麦粉烙饼,饼面焦黄,散着微弱的香气;几个瘦弱的男人则挥舞着借来的铁锹,试图在冻硬的土地上挖出水渠。孩子们追逐着一只叼着骨头的野狗,跌跌撞撞,泥水溅了一身。
赫利站在营地中央一辆破旧牛车旁,成了这群流民的支柱。她身着皮甲,腰间短剑微微反光,头简单扎在脑后,脸上满是风尘与疲惫,手里攥着一卷粗糙的羊皮纸,上面潦草记录着新村民的名单、分配的土地和物资。她眉头紧锁,目光扫过营地,试图在混乱中理出头绪。几个亚美尼亚长老围着她,操着夹杂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口音,争论不休。一位白须老者挥着手,抱怨水源太远,牲畜不足;另一位年轻些的男人则激动地嚷道:“我们需要更多的木材!这些帐篷挡不住夜里的寒风!”赫利深吸一口气,声音坚定却难掩疲惫:“水渠正在挖,木材明天会从托尔托萨运来。你们得先把地开出来,春天就能种上小麦!另外,我还会在这里搞一个白纸作坊,我会让大家过上安稳日子的。”赫利的话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却也透着对同胞的关切。
李漓站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赫利的背影。他一身沙陀人的长袍,双手抱胸,脸上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在他的担保下,这群亚美尼亚人才得以安顿在卡莫村及周边,填补塞尔柱人撤离后的人口空缺。然而,赫利如今满心扑在安置新村民上,忙得连和他喝杯麦酒的时间都没有。李漓摇了摇头,低声自嘲:“这女人,怕是把我也给忘了。”
渐渐的,卡莫村在冬日黄昏的薄暮中喧腾起来。寒风裹着地中海的咸腥味,拂过村口的石墙与泥瓦房,空气中夹杂着柴火、烤饼和牲畜的气息。一支车队浩浩荡荡驶入,更将这小村推向高潮。车轮碾过冻硬的土路,吱吱作响,马蹄踏地,扬起尘土,铃铛叮当,引得村里的孩子和野狗追逐着喧嚣而来的车马。
车队足有七八辆马车,装饰各异,有的车厢裹着粗麻布,有的镶着铜片,雕花木框在夕阳下闪着微光。车夫吆喝着,挥舞皮鞭,马儿喷着白气,步伐整齐。村人纷纷探头,妇人们停下汲水的活计,孩子们踮脚张望,窃窃私语:“这是哪来的贵人?”车队径直驶向村子深处李漓的旧宅,那座半木半石的宅邸,虽有些年头,却依旧气派,门前两棵老橄榄树在风中摇曳。
李漓正在宅院里翻看一卷羊皮卷书籍,忽被院外的喧嚣惊动。他推开木门,踏出门槛,迎面便见车队停在宅前,尘土未散,车上下来一群女子,衣着华丽,风尘仆仆却难掩风姿。莎伦、梅琳达、哈达萨、玛尔塔、迪厄纳姆、帕梅拉、苏麦雅——这些曾与他同欢共苦的伴侣,竟齐齐出现在眼前!她们个个面带笑意,眼神或娇媚或戏谑。
“莎伦,你终于回来了!”李漓快步上前,握住莎伦的手,喜悦溢于言表。
最引人注目的,是莎伦。她一袭深灰长裙,腰间系着镶银丝的腰带,乌盘成复杂髻,怀里却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孩。那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裹在柔软的羊毛毯里,小脸粉嫩,睡得正香,细密的睫毛微微颤动。莎伦低头轻哄着女儿,脸上满是母性的温柔,抬头见李漓,眼中闪过一丝眷恋,笑道:“少爷,你想我回来,我当然得回来。安托利亚的生意转给别人了,我打算在这儿开个店,好好陪你……还有我们的小妮子。”她轻轻晃了晃怀中的婴孩,语气轻快却带着骄傲。
李漓怔了一下,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那名熟睡的女婴脸上。她小小的身子蜷在莎伦怀中,鼻翼轻动,唇角微张,仿佛梦里还在吮着乳。李漓心头一热,一股柔软的情绪不由得漫上心头。他快步走上前,轻轻握住莎伦的手,脸上是难得的温柔神色:“莎伦……她是……我们的女儿?”李漓低下头,想去碰一碰那稚嫩的小脸蛋,又生怕吵醒她,手指悬在空中僵住,样子格外笨拙。
莎伦忍不住轻笑出声:“当然是啊!我给她起名叫‘艾米莉’。不过你要不要也给她一个震旦的名字?”
“李萩。”李漓笑着说出那个名字,声音低而温柔,仿佛怕吵醒小小的艾米莉。
莎伦轻轻重复了一遍:“李萩……真好听。对了,阿贝贝生了个儿子,她自己给孩子取了阿姆哈拉名字,叫铁沃德洛斯,阿贝贝说一定要你亲自给他起个震旦名,还让苏尔家的商船把信带回去。”
“儿子?”李漓一愣,转而笑道,“和她一样黑乎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