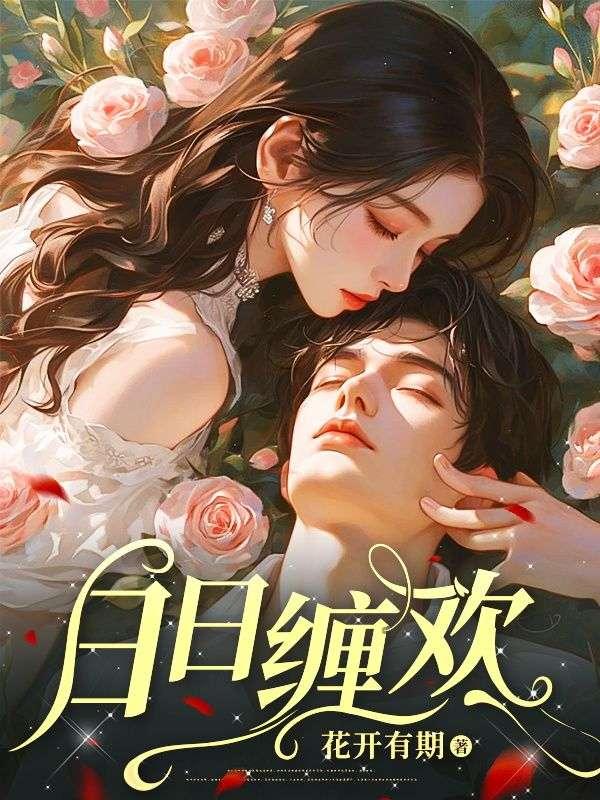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本将心向沟渠 > 缝补(第3页)
缝补(第3页)
顾濯却避开她的目光,迈步朝书桌走去。
他走得不疾不徐,似乎与往常无二,但祁悠然敏锐地嗅出一丝不对劲。
念头未落,手已先动了。
她一把攫住他垂在身侧的手指。
一片冰冷。
温热猝不及防贴上,顾濯像是被她这番举动惊到了,带着一种近乎狼狈的决绝,他猛地一挣,把手抽离开,人也向后急退半步,和她隔开些距离。
就在这衣袂翻飞、气息交错的瞬间,祁悠然却闻到了掩在衣袍下的一丝药味。
“你……是不是寒毒又发作了?”她的声音在颤,转身扑向窗棂,手忙脚乱地要关上那扇窗。
她清楚那蚀骨的滋味,周身寒意缠绕,五脏六腑都似被无形的细针扎过,而这份苦楚,顾濯硬生生捱了三年。
……都是因为她。
顾濯垂眸,睫毛遮住了所有翻涌:“没有。只是近日公务冗沉,略感疲乏,喝了碗安神的汤药罢了。”
他看向祁悠然,对方失魂落魄的愧疚让他心中泛起些懊恼。
他厌恶于看到她自责内疚的伤神,更厌恶自己心底那点因她关切而生的、不合时宜的松动。
“我说过了,莫要做多余的事。”他平了平心绪,再次一字一字强调。
末了,目光掠过她手上的素帕:“你……若无别的事,就回去吧。”
祁悠然手指蜷了蜷。
像是下定了决心,她眼皮一抬,那目光便活脱脱成了两尾湿漉漉的鱼,在冰冷的空气里徒劳地扑腾着,挣扎着要跃进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去:“后天……是我的生辰,你……能不能,拨冗陪我……用顿晚膳?”
后天……
顾濯没言语,脑中闪过许多思量。
可对上她眼睛时,却顿住了。
——她的眼圈竟红了。
红得那样突兀,那样不管不顾,像那年冬天,她莽撞递过来的那枝梅,灼灼地映着雪光,烫了他的眼。
拒绝的话,突然就哽在了喉间,一个字也吐不出。
“……好。”他听见自己应下。
祁悠然朝着他,缓缓地、用力地扯开一个笑容。
那笑容绽放在她带着泪意的脸上,明媚得有些失真。
好看的眼睛弯沉沉的,如同水中破碎的月牙,泪光在她眼里碎成了星子,晶晶亮亮地闪烁着,映着一点残存的天光,也映着一点摇摇欲坠的指望。
天昏地老的爱情仿佛在这弯笑中荡漾。
后日的黄昏,我便来缝补那些过往的错处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若是不肯,也罢。
横竖窗格子底下,我自会挪着步子挨近些。
那敲门的响动,一声,又一声,总是我的。
毕竟,我的悲欢,已然经不住半点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