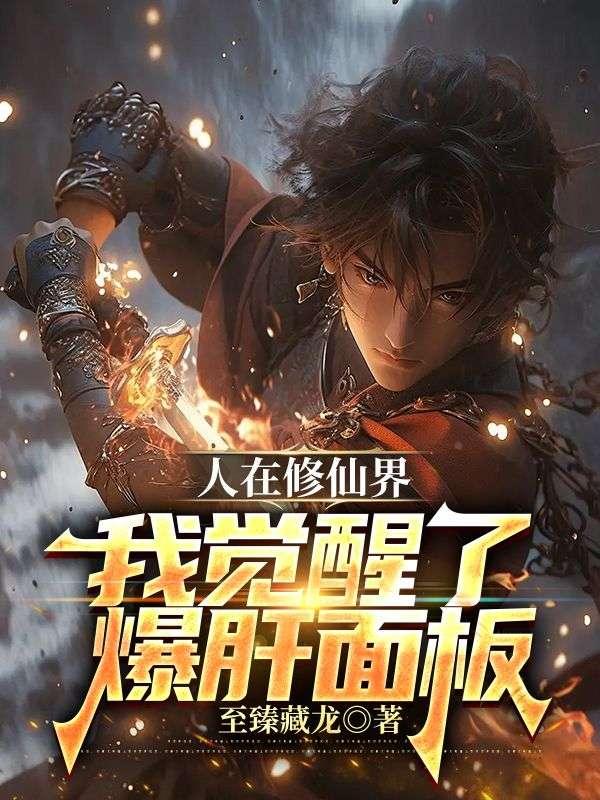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本将心向沟渠 > 戛然(第1页)
戛然(第1页)
指甲深深掐进皮肤,祁悠然没有说话,压下心中的歉意与酸涩,只仓皇地接过那方帕子。
“婚期既定了,横竖也没什么可商议的,一切……但凭侯府做主便是。”她转过身,“若没有事,你便回去吧。”
她能感受到一道目光静静落在后背,带着探询与某种她不敢深究的余温。
她僵了一瞬,却固执地没有动。
良久,顾濯似是轻轻叹了口气,脚步声远去。
殿内便只剩她一人。
她慢慢蹲下身去,攥紧了那方帕子。
裙裾萎靡地铺开,像一朵被霜打湿的花。
起初只是无声,后来那呜咽便再也压不住,断断续续地从喉咙深处逸出。
。
十里红妆,铺天盖地。
是泼天的繁华,亦是泼天的虚妄。
祁悠然恍惚地坐在轿子里,眼前只有一片混沌而压抑的暗红。
赤金的凤冠,珠翠的步摇,累累赘赘地坠在头上,压得她颈子酸,额角胀,嘴角也沉沉地向下耷拉,扯不出半分新嫁娘该有的喜气。
热闹都是旁人的,外头的吹打喧天,锣鼓铙钹敲得震耳欲聋,她却只觉得吵闹。
轿身猛地一顿,落了地。
帘外伸进来一只手,骨节分明,修长有力。
她闭了闭眼,将酸涩与刺痛收回,伸出手,冰凉的指尖轻轻搭了上去。
掌心渡过来的暖意,像煨着药罐子的文火,慢悠悠,温吞吞,笃笃地熬着。
一股子厚重的苦味,就这么丝丝缕缕地钻进她的心里。
她却舍不得放开。
走慢些,慢些吧……
她卑微地乞求着。
心在炙烤,她却是欢喜的。
她知道,这欢喜迟早要褪色、要斑驳、要连本带利地偿还给无情的时光。
可此刻,她宁愿闭着眼,饮鸩止渴,让这点带着毒性的甜,在舌尖多停留一刻,哪怕下一刻便是肝肠寸断。
。
圣驾亲临,恩宠非凡。
侯府内外宾客如云,煌煌赫赫。
司仪扯着嗓子开口。
就在这万众瞩目、礼乐齐鸣的顶点,新娘却猛地抬手,扯下了那遮天蔽日的红盖头。
珠翠碰撞,叮当乱响,金玉的哀鸣响彻喜堂。
满堂的喧哗骤然死寂,所有目光都惊愕地聚焦在她身上。
她的肩膀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苍白的脸上,唯有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臣女祁悠然,今日冒死,状告当朝丞相林枫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