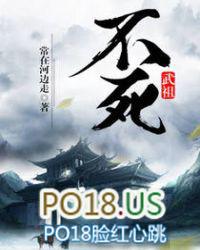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不是满级重生吗 > 长公主府(第2页)
长公主府(第2页)
就这样,北野肆依旧不甘心,他还要在上书房处处胜自己一筹。连本是父皇钦点给他的老师——柳太傅,也更喜爱北野肆。
三年前北野肆离京养病,原以为这碍眼的人终于要消散在江南烟雨里,谁知那具残破身躯偏要挣扎着回到京师。
一个病秧子,还妄想抢夺皇位,简直痴人说梦。
湖心亭四面的纱幔被夜风吹得簌簌作响。
北野稷顿了顿,咬牙道:“北野肆和他那个苗疆母妃,都令我作呕。只有孤,才是北国最正统的、唯一的太子。”
坤仪挑眉:“肆儿和你一样,都是皇兄的血脉,北国的皇位从来都是贤者居之。”
“就凭那个咳血咳到连弓都拉不开的病秧子?”北野稷不屑,微微一笑道:“不过无论是我还是北野肆,都轮不到江辞尘。”
坤仪平静道:“本宫和辞尘不参与储君之争。”
北野稷道:“那您为何处处与我作对?您对江辞尘的偏爱,已经到侄儿都要怀疑,您是不是想要将我拉下来,把储君之位送给江辞尘了。”
坤仪喝道:“太子慎言!”
“孤慎言,长公主才要慎行,您别忘了——”他刻意拖长了语调:“江辞尘身上,流着一半谁的血。”
坤仪骤然变色,眸中怒火翻涌,猛地抓起案上白玉酒杯,狠狠朝北野稷砸去!
“闭嘴!”
酒杯擦着北野稷的鬓角飞过,重重撞在庭柱上,“砰”地一声闷响,反弹回来滚落在地。
北野稷不躲不避,佯装恍然大悟,继续道:“哦,您怎么会忘呢?”
他盯着坤仪那张因震怒而微微扭曲的脸,一字一顿道:“当年,可是您亲手……”
“滚!”坤仪暴怒,指着北野稷厉声骂道:“滚!本宫命你现在就滚出长公主府!滚!给本宫滚!”
她声音尖锐,几乎撕裂了庭院的寂静。
远处的女官闻声慌忙赶来,小心翼翼地扶住她颤抖的手臂,低声劝慰:“殿下息怒……”
北野稷冷眼看着坤仪失控的模样,缓缓道:“姑母‘突发恶疾’,侄儿特来探望,如今看来——”
他微微颔首,眼底寒意森然:“您的病,真是越来越重了。”
说罢,转身离去。
*
刑部大牢的阴湿气息裹挟着血腥味扑面而来。
“太始院每年集资一次,以为皇帝祝寿的名义,在灯花节请僧人进香,为何朝廷的贡品会不翼而飞,最后出现在红楼拍卖会上?”
被审问的人被铁链呈十字形捆在木架上的,他嘴角的血迹已经干涸,却仍扯出一个讥讽的笑容,除此之外,一言不答。
陈北辙又一鞭狠狠抽在被审的人身上:“去年灯花节,太始院‘请’走的南海珍珠、西域香料,恰巧出现了在那月的红楼拍卖上。据我所知,所有买家,都在当晚留宿京师花楼。”
被审的人缓缓抬头,露出一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
牢房外的过道里,最后一盏油灯将熄未熄。
他看清那人静坐在一张榆木圈椅上,修长的手指轻轻搭着扶手,指节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冷玉般的光泽。
高挺的鼻梁在另一侧投下狭长的阴影,将那标准的桃花眼藏在黑暗里。
狱卒提着灯笼走近:“大人,三更了。”
光晕晃过江辞尘束发的玉冠,几缕散落的发丝被照得发光,衬得肤色愈发白皙。
他没有应答,只是略微抬了抬下巴。
这个动作让他整张脸完全暴露在烛光下,剑眉入鬓,眼尾微挑,本该是多情的相貌,却因眸中那潭死水般的平静而显得格外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