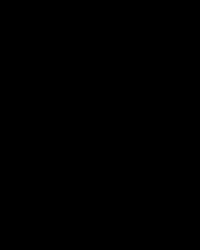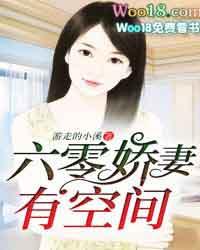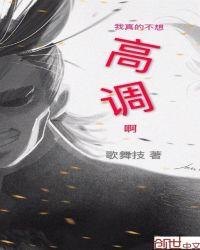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桃夭定终身-高冷帝君漫漫追妻录 > 自难忘(第3页)
自难忘(第3页)
郑忽如何不知朝堂下波涛汹涌?权利更迭,要么杀一片重新换血,要么不计前嫌稳定局势,郑忽选择了后者。如此过了几月,郑国的局势才慢慢缓和下来。
这边郑忽入了郑城,得知齐国大军由当今齐王亲自率领候在城外,忙下令在城外大享齐军。复辟成功,齐国背后的支持是关键。他又托人给诸儿私信,邀他到郑宫赴宴。
五月的风已经有夏的味道,诸儿由人领着,第一次踏入郑宫。曾经称霸多年的郑宫并不似想象中巍峨,大约是近年来王位更迭疏于整修的缘故。
远远地看到一座宫殿,里面有影影绰绰的灯火,待诸儿走近了,里面似有淙淙的琴声飘出。侍卫按吩咐送到此处就停住了,诸儿一人继续朝前走去,那曲调十分熟悉,和自己听过的又不太相同。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
殿里面有人正在低头抚琴,诸儿没有佩萧,便轻轻跟着那琴声吟唱,直至琴声渐轻,乃至最后消退于静寂。
郑忽抬头迎上诸儿,诸儿身穿盔甲,头戴缨帽,疲惫的眼神里有遮掩不住的喜悦,待走近了,那喜悦隐退又变成了心疼。
几年时光,郑忽变得消瘦,虽正值壮年,两鬓已灰白相间,那是潜逃异国、卧薪尝胆的岁月侵蚀的证据。
诸儿大步上前,用力拥抱郑忽,似要用这拥抱给这昔日战友一些温暖和慰藉。郑忽起初是僵硬的,可诸儿的拥抱坚定而绵长,和之前那些一触即开的拥抱又不同,隐藏多年的渴望被唤起,郑忽的回应热烈起来。
诸儿望向郑忽,郑忽狂热的眼里有泪光闪烁,诸儿隐隐觉得哪里出了错,他们是多年未见、惺惺相惜的战友,怎么这会儿倒似久别重逢的情侣?
他拍了拍郑忽的肩膀,大声笑道:“郑兄,你若再不见我,我可要率着大军冲进你这金殿了!”
郑忽刚刚那片刻的游离转瞬即逝,他很快收敛自己的情绪,笑着说:“这不就见上了!贤弟,几年不见,如今你已是齐国国君了!”说罢,拉着诸儿入座,美酒佳肴已早早备好。
夏夜的风熏得人沉醉,岁月的凶险和磨难在这一刻都化为下酒的佐菜,两人不紧不慢地喝着酒,时而郑忽说诸儿听,时而又换成诸儿倾诉郑忽倾听。
郑忽说起几次他在卫国被不明人物伏击险些死掉,诸儿说起夷仲年离世、父王神志昏迷那一年他的脆弱和煎熬。
郑忽又说道后面如何安抚群臣、追击子突的计划,诸儿也提起稳卫围纪、步步为营的想法。
诸儿觉得如今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可以懂得自己的孤独和野心,还能并肩去面对未来的凶险和荣光,自己是何等幸运。
他举杯对郑忽说:“老天究竟待我不薄!郑兄,幸好有你。不然这帝王之路该何等孤独?”
郑忽心中亦有万千感慨,他不言语,只是对着诸儿举杯,诸儿摇手说道:“不能再喝了,再喝今晚就真的走不出这金殿了。”
郑忽停了一会儿,说道:“那就留下来,我们就借一借今夜的月光,互诉衷肠。我的美酒还有很多,贤弟,今晚一别,相逢不知何时,我们且不醉不归吧!”
这一夜,两人不知喝了多少酒。次日天蒙蒙亮,郑忽到城外送别诸儿,诸儿离齐已有一月,国事纷纷,如今郑国局势已稳,两人只得互道告别。
诸儿着急回齐,一件重要的事,也是藏在他心中多年的打算,便是重修法令。他做太子多年,除了战场征伐,齐国的疆域,从齐卫交界到东海之滨,这些年他不知跑了多少次。
初时是父王的要求,后面他慢慢知道开疆扩土只是第一步,治理好这一村一邑,才是国之永昌的秘密。而治理好这一村一邑,虽然要因地制宜,但也要有共同的法去约束和规范,朝堂的政令才能上令下达。
如今他是齐国的王,他要亲自书写齐国的法条,把他的政令一步步推下去,从繁华的临淄到蛮荒的东夷,这任务虽然艰巨,他下了决心要去做到。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几年有些公子大臣,仗势欺人,是时候惩戒约束了。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令还需做得更简洁易行些,最好能让百姓能张口就来,知道上面在鼓励什么又在禁止什么。
“尽地力之教。”开荒还要继续鼓励,若百姓开了荒,新的地可归开荒者所有,官府不仅若干年内不对荒地征税,还要提供农具、种子,协助开荒。
“善平籴。”这个在临淄他已推广多年,丰年官府平价购进粮食用来平物价和备荒;荒年再出售或出借防止有人囤积居奇,有人饿死街头。这些政策的好处显而易见,但需要专门设置官员去推广和治理,如此还要国家投入不少人力。
齐宫的朝堂上,围绕着新的法令大家群情激昂,争论着、建议着、唇枪舌战着,诸儿不仅不阻止,还笑说法不辨不明,鼓励大家尽管说出真实想法。
这些年走来,他早已学会如何去驱动和平衡这些力量了。虽然他新为国君,但朝堂上下无人敢质疑新王的威望和能力,相反,许多人对国家的未来,前所未有地更多了一些期待。
群雄逐鹿,属于齐国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