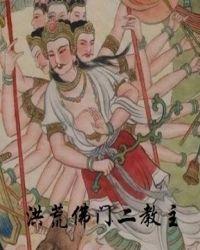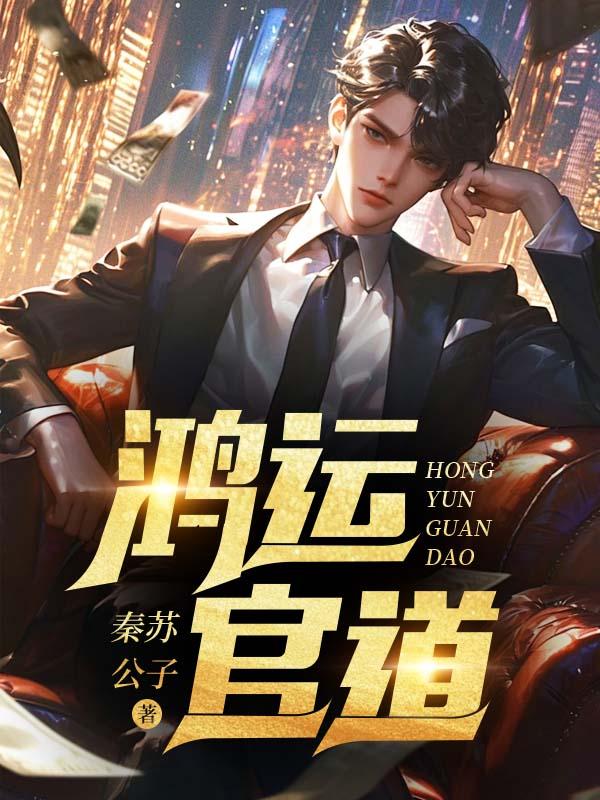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春色满棠 > 第427章 害怕他死了(第1页)
第427章 害怕他死了(第1页)
宫门口已经备好了马车。
马车往将军府赶时,孟梁安忍不住问太监:“公公,到底出了何事?”
她心里的预感很不好。
太监犹豫了一下说:“是沈世子回京来了,受了伤。”
孟梁安意外得愣了下,之后心瞬间提了起来。
两个孩子感受到了她的紧张担心,仰头问:“母亲,爹爹怎么了?”
马车摇摇晃晃,孟梁安下意识把两个孩子往怀里箍紧了些:“…严重吗?”
太监宽慰道:“县主不必担心,王爷已经传了大夫去给沈世子医治。”
不直接回答,。。。。。。
夜风穿廊,吹动檐下铜铃叮当轻响。孟梁安立于春棠总馆后院的药圃之中,指尖拂过一株新开的白棠花,露珠滚落,沾湿了她素色衣袖。远处城楼更鼓三声,已是子时。
她未回房歇息,只披一件旧斗篷,在石凳上坐下。案几上摊着南诏带回的残卷??那张描绘炼药坊结构的草图已被反复摩挲得边缘起毛,墨线模糊。她凝视良久,忽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小片赤纹锦布,与图中所绘一致,只是染血处已成褐斑。
“三百具尸骨……”她低语,“可丙仲康真的一人担下所有罪孽?”
背后脚步轻悄,知棠提灯走近,见母亲独坐寒夜,忙将披风覆上她肩头。“您又在想他?”她轻问。
孟梁安点头:“丙仲康行事狠绝,却极重因果。若非心中有执念深如渊海,断不会以活人为炉鼎,炼这逆天之药。我一直在想,他为何偏偏选中春棠为敌?仅仅因先帝废其医官之位、贬为边民?还是……另有隐情?”
知棠沉默片刻,道:“阿枝昨夜翻查壬戌案旧档,发现一件异事:丙氏一族原非南诏土著,而是百年前从中原来的流徙医户。他们祖上曾是太医院御药局副使,因私改御方致妃嫔暴毙,全家被贬岭南,后辗转迁至南疆。”
“御药局……”孟梁安眸光微闪,“那正是我外祖父执掌过的部门。”
两人对视一眼,皆觉脊背生寒。
若丙家与孟家曾在朝中共事,甚至同研医术,那这场延续三代的仇怨,或许并非始于权力倾轧,而是源于一场被掩埋的医案??一场关于生死、伦理与信念的根本分歧。
知棠压低声音:“我在父亲留下的日记里找到一段话:‘丙公尝言,疾不可治者,当断其根;病入膏肓者,不如速死。吾驳之:医者但求延一线之望,岂能代天判生死?’”
孟梁安闭目,似有旧影浮现眼前。她记得幼时听母亲讲起过一位姓丙的老医,性情孤峭,擅用毒攻病,曾以烈药清瘟疫村,七日灭疫,也七日屠村。朝廷褒其功,百姓畏其名,称其“鬼手仁心”。
“原来是他。”她睁开眼,“你外祖母当年反对他主持西北防疫,认为其法太过酷烈。后来那场瘟疫确实平息了,可整座玉门屯堡无人幸存。丙仲康因此被革职流放,临行前留下一句话:‘今日你们说我残忍,明日必有人哭求我归来。’”
风忽止,万籁俱寂。
“如今,他回来了。”知棠喃喃。
孟梁安起身,走向药圃深处。那里有一口封井,青石板上刻着“壬戌禁水”四字。十年前火灾之后,此井便被永久封闭,因检测出含有微量青蚨涎,疑为丙党投毒之所。
她蹲下身,手指抚过石缝间渗出的一滴水珠,轻轻嗅了嗅。
“不对。”她忽然蹙眉。
知棠连忙取来银针试毒,插入水珠中,须臾抽出,针尖泛出淡淡紫晕。
“不是青蚨涎。”老陶不知何时出现,拄杖而来,“这是‘冥露’,产于极北冰窟的阴寒之液,传说出自千年冻尸眼中泪滴。服之无味无形,却能诱发梦魇、幻听,久用则神魂离散。”
孟梁安眼神骤冷:“这不是南诏的东西。这是北地秘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