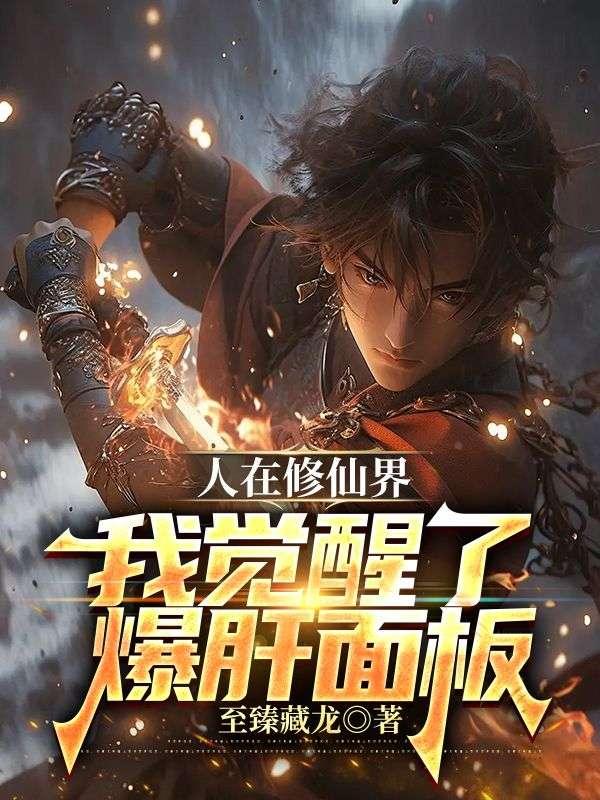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发梦蜉蝣 > 第 61 章VIP(第2页)
第 61 章VIP(第2页)
林晋慈推开院门。
穿过前院的小路,她忽然想,她可能也遇到了她人生里的环保项目,十分珍爱地围绕她展开禁止破坏的构想,可能主题也叫呼吸。
当晚宾主尽欢。
傅易沛异常高兴,多喝了几杯酒,撑不到散席就被劝去楼上休息,难得一聚,还是傅易沛亲自下厨,其他人也没少喝。
夜深时分,热闹也渐渐沉寂。
别墅常住的两个佣人迅速将杯盘狼藉的餐区清洁如新,林晋慈在她们的帮助下,了解客房的情况,给留下的客人安排住宿。
等所有人都离开,她关了客厅的灯,缓缓上楼,想要看看傅易沛情况如何。
主卧没开灯,只有旁边的浴室里映出一小片光。
晚上还穿在傅易沛身上的藏蓝色圆领毛衣,此刻被丢在靠近浴室的地面上,林晋慈上前捡起,刚起身,听到里面哗哗的水声停了。
潦草穿着睡衣的傅易沛,微微踉跄着走出来,上衣前的扣子一粒没扣,不自然的呼吸起伏,带动腹部的薄肌,头发好像也只胡乱擦了两下,搭着一块小毛巾。
看到林晋慈,便朝她走过来,几乎是不知轻重地撞到林晋慈身上来,头上顶着的毛巾要掉,被林晋慈一把抓住。
他整个人压下来,林晋慈试图撑住他的动作大概是被理解成推开,于是喝醉的人不太高兴,把她抱得更紧了,气息灼热地贴在她耳边,说些不着调的甜言蜜语。
现在,林晋慈可以完全确定,这个远远看去雕栏玉砌的人,内部真的有一根粉色乐高拼成的柱子,别人看不到,是因为可能只对她开放了观看权限。
傅易沛
后颈的发根还是湿的,林晋慈一边听,一边用毛巾擦着,直到肩膀被抵得酸麻不已,才出声问他,要不要去床上?
傅易沛说“好”。
却似乎误会了林晋慈的意思,手臂没有松开林晋慈的腰,反倒逼近。
林晋慈别扭地跟着傅易沛的脚步倒退。
问他要干什么,他并不说话,随后一阵天旋地转,林晋慈后脑重重跌进松软床铺。
院子里夜间长明的灯光映在床边,明与暗清晰切割,她的眼睛恰好在明区边缘,如同蒙上一条光带。
可以清楚看见压在她身上的傅易沛,以及他每一个动作。
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专心致志地低着头,将林晋慈身上的丝绸衬衫从腰带中拽出,一粒粒解开小小的扣子,然后俯身,将自己酒后高烧般的体温传递给她,细密地吻她的肩。
一寸寸吻,也一寸寸将碍事的肩带拨下。
暴露在微冷空气里的肌肤,如薄纸一样起伏着,不期然被吻,蜷缩起来,又像被火焰烧透了。
遥控器发出“嘀”的一声响。
他们陷入窗帘渐渐合拢后更纯粹的昏暗里。
次日一早,傅易沛神清气爽地醒来,赤脚下床,将窗帘掀开一角,银装素裹的园景映来刺眼的光线。他又将窗帘搭回去,自己也折返床边,跟林晋慈挤在同一块枕头上,亲林晋慈的脸,轻声告诉她,外面下雪了。
林晋慈半梦半醒着,哼着睡意浓浓的鼻音。
傅易沛侧着身体,又靠近过去,在她耳边问,喜不喜欢雪人?
她似乎没听清傅易沛在说什么,眼睛都没睁开,扭了几下,贴到傅易沛怀里,将他紧紧抱住,说喜欢。
这场雪,断断续续下到年前才停。
林晋慈放了假,但没有回宜都的打算,黑名单里的电话无法拨进来,除夕夜被喊去小姨家吃饭时,本以为少不了听一通劝说,却意外没有。
林晋慈用热水烫碗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