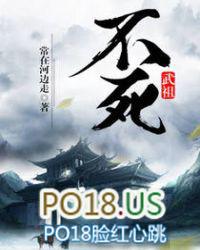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别青山 > 170180(第26页)
170180(第26页)
程荀时刻观察着胡婉娘的状况,见身后没有回应,有些烦躁地朝她吼道:“还不快去!再晚一步她就没命了!”
陈婆子恍然回神,连连点头,手忙脚乱地爬起身往外跑去。
陈婆子慌乱的脚步渐渐远去,林间又恢复了平静,除却飞瀑落水的哗啦声,只余程荀粗重而疲惫的呼吸。
程荀眉头紧皱,重复着按压她腹部的动作。午后,山间日光正烈,炽烈的光线直直打在程荀身上,刺得她睁不开眼,脸上温度渐渐升高。
她浑身酸痛,手臂几乎麻痹,眼睛紧紧盯着胡婉娘的脸,心中别无他想。随着她起伏按压的动作,不断有水珠滴落顺着下颌滑落,已然分不清是汗还是水。
不知过了多久,胡婉娘上身抽动,哇的一下吐出了一口水,而后呼吸逐渐平畅,苍白的脸上眼皮微动,已有了要醒的迹象。
程荀骤然松了口气,脱力地移开身子,双手撑在身后,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头顶飘来一片云翳,天光变暗,林中乍然起了一阵风。林间草木摇动,飞溅的瀑布随风而动,水雾飞向岸边,仿佛雨丝细细密密落到程荀脸上。
程荀浑身湿透,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刚想起身看看陈婆子可带人来了,目光掠过胡婉娘的身体,却顿住了。
山风吹起胡婉娘的衣裳,她的衣袖被风卷起,露出了一截手臂。而那瘦削而光洁的胳膊上,却突兀地露出了些许痕迹。
程荀在她身旁蹲下,依次拉开她两只衣袖,只见她双臂上竟布满了各式的伤疤。
要么是青紫的淤痕,要么是尖锐器具划过的细碎伤口。大部分伤口都已陈旧,只余一条条新长出的淡痕。最醒目的却是手腕处,有一道刚刚结了血痂、还泛着红的刀疤。
程荀握着她的手腕,不自觉抿住嘴唇。
有些淤青像是他人所为,可那些尖锐利器所伤的疤痕,却多半是她自己所为。
更莫说手腕上那道疤。
这五年,她过得并不好。
也是,一个娘家男丁悉数死在狱中、母亲又沦落为官妓的女子,背后没有任何支撑,婆家又能给什么好脸色?
若是所嫁是个正直善良、真心待她的人也就罢了。
可她比谁都知道,张子显本就是个道貌岸然、□□熏心的小人,胡家尚且如日中天时都敢阳奉阴违、图谋算计,更莫说如今胡家倒了,他又怎会好生待她呢?
胡婉娘从小便是争强好胜的性子,做人行事向来愚蠢、短视,后宅里的手段,也不过仗着地位强压旁人这一条。
落入张家手中,除却能勉强给她一方遮风避雨的屋檐,也不过徒增折磨。
程荀神色怔怔,不知想起了什么,耳边却响起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没死……”
程荀抬头望去,却见胡婉娘已醒了过来,迷离发痴的眼神直直望着天上,口中呓语,似乎还未反应过来。
下一瞬,她视线一转,目光落到程荀身上。
对视的瞬间,程荀看见她目光先是有些疑惑,而后双目震颤、神情错愕,死死盯着程荀的脸。
她嘴唇翕张,想说什么,可喉咙像被哽住,半晌都说不出话来。
“你……”
沉默的片刻,身后隐隐传来几道急促的脚步声,踏着水畔高高的芦苇与湿软的泥地,深一脚浅一脚,匆忙跋涉而来。
“阿荀!”
身后遥遥传来晏决明的声音,程荀嗓子被水呛过,有些嘶哑地回道:“我在这儿!”
脚步声越来越近,不多时,繁茂的草木中先后冲出几个人影。
晏决明一眼看见全身湿透、衣裳紧紧都贴在身上的程荀。
春寒料峭,微冷的山风吹得她面色苍白,身子不住打颤。
见状,他周身气度一冷,一面脱下外袍,一面飞快奔到程荀身前,长臂一伸,便将程荀捞进自己怀里,用外袍牢牢裹住。
程荀蓦然落入怀抱中,后背被他搂住,轻轻一抬,程荀便被他打横抱起。
而贺川与天宝紧随其后,快步围过来,满脸焦急。
“将她一起带走。”
程荀浑身酸疼,也不避讳什么,有些脱力地靠在晏决明胸膛上,对贺川吩咐道。
贺川看了眼她身后,心领神会。今日宴席,贺川着了一身衣裙,实在不便脱下,只能让天宝脱下外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