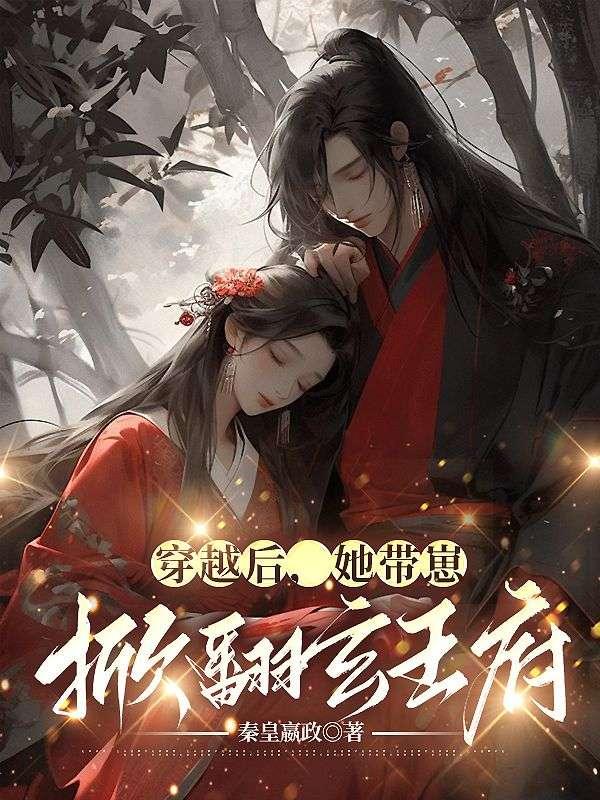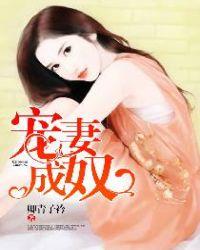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江湖与彼岸 > 都市之狼 八十年代先锋诗歌诗评三篇(第1页)
都市之狼 八十年代先锋诗歌诗评三篇(第1页)
一。《疲惫的追踪》--对谢冕晚近诗评的批评
《百家》1988年第4期
作者:包临轩朱凌波
如果这篇短文伤害了谢冕先生,我们将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安一一作者题记
谢冕作为“朦胧诗”(也称力“第二代”)的首席评论家已经成光辉的定格。但他试图继续充当“朦胧诗后”(也称第三代”)理所当然的评论家的努力无疑是失败了。虽然他的真诚令人感动,但冷酷的艺术铁律告诉我们,他的选择注定是一次悲剧性的选择。同时也预示了“第三代”在现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可能性前景,诗歌的新浪潮必将诞生自己的代言人!遗憾的是,谢冕先生仿佛还未意识到这一无情的理论现实,依然沉浸于逝去年代的激情中……
当“朦胧诗”在文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带高原后,应该说谢冕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特别是“朦胧诗后”的新诗潮从一场默默的反向地下运动终于突破压制已久的传统巨石喷涌而出并漫延开来时,我们惊奇地注意到谢冕几乎是不加思索地迅速投身到这股燃烧的地火中,不管它能燃向哪里能烧多长时间,他的神笔都奇迹般地泪泪流消出赞誉性的文字。令人困愕的是它未免流得太快太猛了,迷失了基本流向和彼岸意识。纵观他关于“朦胧诗后”的评论文章,我们只能客观地说它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准确性和穿透力一一首先是对“朦胧诗后”资料占有的严重不足抑或是置身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无所适从。多是蜻蜒点水,隔靴搔痒。如对“大学生诗派”亦称“校园诗”的评估,以非凡的勇气从极少的缺乏代表性的实证中竟然提炼出具有普遍效应的形而上结论。给入以匆忙草率之感甚至投机取巧之嫌!
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历史性。事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向艺术本体回归“朦胧诗”与近几年向生命个体皈依的“腾胧诗后”第三代,实际上处于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尽管时间跨度小,但艺术探索更迭期的缩短却是有目共赌的。这里暂且撤开更迭期的艺术质量不谈,而谢冕的艺术思维模式并来适应这种更迭期发生相应的裂变,他仍以八十年代初的审美标准来测量“第三代”,一往情深地追赶新诗潮的走向。这不可避免地使他在评论的旅途上疲惫不堪!
由于社会的、心理的、生理的和历史的等诸种因素的断层,实际上他对“第三代”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艺术行为已经相当陌生与隔膜了。而在公开的言论中他仍自诩为理解他们,总是以关注北岛们的心态和口气同这群“嬉皮士青年”对话,痛苦的是,对话了,却未产生真正的交流和沟通。
不客气地讲,其实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迷惘和惶惑,这就使他所谓的理解显得十分苍白;激起的反响也是微弱的。因为时代背景、艺术氛围、诗人群体和读者结构都发生变异了。
他对“第三代”诗歌精神的茫然,最充分地体现在他误认为在中国现代诗歌荒原上众多的探索群体中必将诞生所谓的大诗人。这恰恰与第三代的艺术追求背道而驰。因力“第三代”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普通的人。他们的诗是一种类似生活方式的深刻,诗只是一种精神渲泻和寻找心理平衡的手段。而且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严峻地提醒我们,艺术的高峰体验也只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所以他的美文式的评论文字下面,透露出艺术哲学的陈旧和评论语言的浮华。尤其令人不舒服的是他对自己那种九曲回廊式美文的不厌其烦的卖弄,理性不自觉地沉沦了,批评主体渐渐消失。
作为一个大评论家,功成名就后的谢冕对青年人的宽容在八十年代尤为可贵。但面对今天鱼龙混杂的新现代主义歌运动,他的洞察力消耗了,贵任心淡漠了,那么轻松而随便地接受了一些青年“诗人”为自己作品写评作序的恳求,给子他们廉价的支持。几乎未加分析地肯定了他们的探索和实验。我们认为不是所有对传统的反叛都拥有价值;并非所有的构筑都意味着创造。作为一个严肃的评论家,其审视力是不应该沉睡的。而谢冕好象把这一重要的艺术准则忘记了。他当初的批判锋芒令人痛心地委顿了。被一杯杯温吞水取而代之了!
谢冤先生,您何以“堕落”至此?恕我们直言,您是太想保持您新诗潮评论家的权威的地位了!
一看到您那踉跟跄跄,力不从心的步履和身影,我们最早对您的崇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同情……
也许您没有想到,您对“第三代”的赞助和支持,却换来他们如此犀利而冷酷的谢绝和指责,但这正最鲜明地展示了“第三代”的先锋性风格!
最后,我们要满怀歉意而坚决地说,谢冕,您应该歇息歇息了!
二。《都市之狼》一一朱凌波的诗
原载1988年《北方文学》
作者:包临轩
三年前,我曾为朱凌波写过一篇评论;
在那篇评论里,我试图为朱一向调子过于压抑、灰暗的诗镀上一层亮色,以便诗人和我们大家都能放松下来,长长地吁一日气。但从他后来发表的诗作看,我想我的祈愿是落空了。事实上,他一直沿着原来的诗歌路子走下去,并把自己的生命体验推到了某种形而上的高度。他的诗正在变成格言式的晶体,说来也是一种很奇特的创作现象:朱一贯推崇本我、反理性、非决定论,他认为生命本身是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过程,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空虚是一回事。但在他实际的创作中,无论是意象的选抒、运用,还是诗歌主题,都具有十分明显的理性主义风格。女读者都不怎么喜欢朱的诗,恐伯原因大都在于此。这就是说,他的诗思并不呈现情感逻辑,并不呈现无意识情绪的自然绵延,而是具有很强的意向确定性和选择性;他的诗歌意图大致可以让人一览无余,不过同时又裹挟着呼啸而来的情绪冲击力。或许,他是以近乎克制的、理性的写作态度,表达自己内心深处那颗反理性的思想内核。只不过,在他自己的意识中,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
朱凌波大学毕业以来,一直处于漂泊不定的动荡生活中,他经历了大多数同龄人未尝遇到的挫折和磨难,并且常常是一波三折。他躁动不宁,左冲右突的天性,似乎很难使他过静如止水的日子,他无法与现实中那种刻板、缓慢、节制的生活方式达成妥协。他天生就是一个从里到外毫无掩饰的“彻底”的诗人,因为生活中的他行起事来,并不尊循常规,他把艺术家无拘无束的自由原则也当成生活的原则,这样,在生活中碰壁、吃亏几乎是注定了的!而他本人对此又似乎猝不及防,毫无心理准备。这样,同生活不断发生冲突、对抗的一个后果就是,他的内心充满不平、痛苦和激愤,他差不多真成了一个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人。这正是艺术心理学、艺术发生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吧?
艺术家同生活常规的矛盾、同生活的不妥协态度,大概正是成就其艺术家的一个重要的主体性根源。正是这种充满浓重阴影的内心,规定了他的诗歌只能是漫漫寒夜中燃烧着的幽蓝的火焰。
朱诗的冷峻气质,使我又一次思考一个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哲理诗或诗歌的哲理性。我很不欣赏哲理诗的倡导者,这是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哲理诗”大多只有哲理,而无诗味,何况,有些“哲理”既不深刻,也不独特,无非是某种哲学教条的修辞化,是一种伪诗,或者说,是由匠人制作出来的?品。但我们似乎并不能由此一概否定诗歌的哲学意味,但是要清楚地知道,这种哲学意味既不来自对哲学的演绎,也不是对生活的干枯无味的抽象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