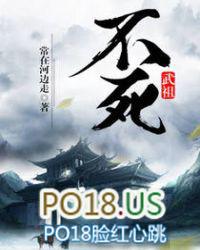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穿越之病美人续命日常 > 第134章(第2页)
第134章(第2页)
冷淡的气质,森然的气度,与那平静到如深渊之感的眼神,无端地讓人感到恐惧。他每走一步,官服上的獬豸就像是换了一副模样,威严的、凶狠的、煞气森森的。
赵瑾下意识腿肚子发软,别看他私底下叫嚣着如何厌恶裴郅,真等见到了人,那便好比是老鼠见了猫,连声都不敢吱一下。
“裴大人,一共是六具尸骨,仵作已初验过,两女四男,一女一男年近五旬,另一女一男三十来岁,余下两男年纪在十七八,六人生前皆是习武之人。”
这六个人,与庄子上的那几个完全对得上。
十六年过去,这些手执屠刀的人已化作白骨。尘封得见天日的真相在这一刻不是喜悦,而是无尽的悲凉。
裴郅看着那堆尸骨,面无表情地示意大理寺的人上前。
“郅……郅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什么人?我父亲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赵瑾问着,却不敢看他。
他慢慢转过身来,看着赵瑾和所有赵家人,目光中没有半点温度。
“他在大理寺的牢中。”
“我父亲他……他犯了什么事?”赵瑾忽地睁大眼睛,“你……你不是中毒了吗?你怎么没事?”
一个说是快死的人,却好端端地出现在这里,而他的父亲一去不回,还进了大理寺的牢中,任是谁稍微一想也知事情的不寻常。
“你……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你想对我父亲做什么……”他因为害怕,而虚张声势地低吼着,“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把你带回来的吗?你忘了他是如何日夜守着你的吗?裴郅……你这个煞星,你到底还要害多少人!”
对于这样的话,裴郅早已麻木。
“害人的人不是我,而是你父亲。”
“我父亲……”赵瑾不信,但此时却没有人为他解惑。
裴郅一个手势,大理寺的人便开始动手抬起那些尸骨。
望着他冷漠的背影,赵瑾几近崩溃,“为什么他总是这样……看不起人,人人却都围着他转,夸他赞他。从小到大,我父亲把他看得比我还重,我不明白,我哪点不如他……”
关云风闻言,讥笑一声。
他自小习武,无数人说他天资过人,他曾打遍京中无敌手。哪怕是这样的他,都不是裴郅的对手,这个草包赵世子也敢说比裴郅强,那他算什么?
“就凭你?也配和他比?”
“我……”
“草包就是草包,永远看不清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他环顧赵家众人,好心地多嘴,道:“天理昭昭,裴家当年的惨案就快要大白于天下,尔等静候圣裁吧。”
一听与裴家当年的惨案有关,还在等圣裁,所有人心中都有不好的预感。哪怕是被骂草包的赵瑾,都顧不上为自己争辩。
大理寺的人走了,关云风也走了,但围住侯府的金吾卫没走。
不过一夜的时间,对于赵家众人而言却是每一刻钟都是煎熬。当天将微明之时,宫里的圣旨终于到了。
赵颇与羅諳施同舟合谋残害冯御史一家,还有裴郅一家的罪名昭告天下,两人被判斩刑,羅家抄家流放,除了羅月素母女。羅月素大义灭亲有功,将功抵过,与柴氏免于流放之罪。
侯府被除爵,因有丹书铁券可抵流放之罚,但却被贬为庶民。几十房人全被赶出来,当侯府的大门贴上封条时,为十六年的悬案划上了句号。
这桩案子的查清轰动整个南安城,谁也不会相到,造成裴家惨剧的人竟然是与之一脉相传的赵家。
赵家人所到之人,围观之人议论纷纷,还有不少人朝他们吐口水。
当他们经过裴府时,赵瑾看着那紧闭的门,已经一片空白的脑子还要想着,他们不是要将这一府的富贵尽收手中吗?怎么一夜的工夫,他们成了丧家之犬?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走,又都是失魂落魄的模样,自然免不了你碰了我,我踩到了你。而不小心碰到他的人,是杨氏的儿子赵平。
赵平身子骨弱,走着走着一个踉跄撞到他身上。哪怕是杨氏还算手快,一把将自己的儿子给拉住,还是免不了踩到他的脚。
他下意识的反應,如平日里一般不掩自己的厌恶,心中戾气瞬间有了发泄的地方,“滚开,你这个讨债鬼,你怎么不早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