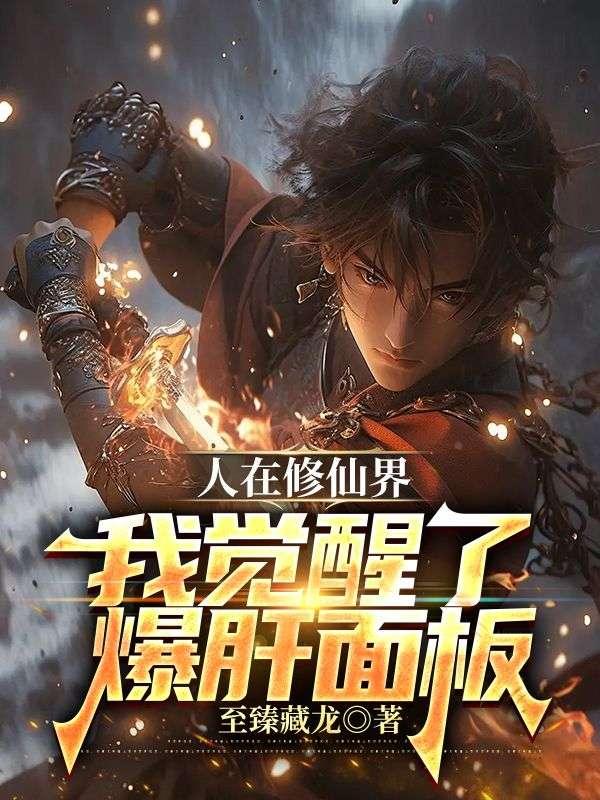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首辅大人的养花守则 > 5060(第4页)
5060(第4页)
过去,她最期盼、最渴求、连做梦都时时惦记的妄念,就是他能心悦于她。
可而今,当她不愿、她不想了,这成了真的妄念竟变为最令她惶恐的东西。
“你这次又是怎么了?又昏了这么多天?”胡照心掰开两瓣橘子,一瓣丢嘴里,一瓣伸过去递给她。
冬宁身子还没好全,不宜在街上久逛,胡照心便登门来看望。
她笑容淡淡地接过,抿出个浅酒窝,耐心地去剥那橘瓣上的经络,“算了,不说了,我这老毛病你也不是不知道,总有些猝不及防的时候,说晕也就晕了。”
现在说起这个怪病,她竟也是云淡风轻起来。
胡照心内心幽叹,但不愿牵起冬宁更多的忧思,觉着她能像这样想开点才好,便也强打精神,把话头引到别的地方去。
胡照心说话顶有趣儿,任它如何淡如白水的故事,到了她嘴里都能脱胎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
冬宁只笑着,静静她说,偶尔附和上几声清脆的笑。
少时,她慢慢敛了笑,扯扯胡照心的袖子,头挨过去同她耳语道:“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帮帮忙。”
“嗯……你说呗,什么事儿这样神神秘秘?”胡照心不耐烦这样压低声儿说话,直起腰又大声吆喝两句。
“嘘!”冬宁示意她噤声,秀眉皱得深,左右张望一圈,总疑心这府里有什么人听墙根。又靠过去,用力晃晃她的袖子,“你且小声点儿,我怕叫人听去了不好。”
直觉她要做什么坏事,胡照心眨眨眼,“要干什么?你说?”
“我……想要搬出去章府,可我也不大懂这找赁屋的事儿,想叫你同我去寻个牙人,再一起上街看看房子。”
她一口气说完,胡照心早已鼓瞪个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她,“你……怎么忽然想搬出去章府?”
“我可是记得,当年那章阁老要赶你出去,你可是轰都轰不走呢!离家出走都要同他闹别扭,怎的现今又变了主意,自己倒主动想要搬出去了?”
怪哉怪哉,她这个朋友的想法,实在叫她看不透了。
冬宁摇摇头,心情复杂,不知该如何同她解释,只好言简意赅道:“你就当是我累了,不想再同他纠缠下去了吧。”
她眉宇凝着浓愁,眼浮轻雾,明丽的五官已完全是个少女模样,不再有少时的无忧,却开始沾染这人世的苦与涩。
“可……你一个姑娘在外头,总是不大好的,这谁放心得下呢?”
“没事,等我找到屋子,孃孃也该回来了,到时候有她在,我便不怕了。”她笑得小酒窝露出,很是乐观地道。
胡照心翻着眼睛想了想,眼前浮现芳嬷嬷那人高马大的壮实模样,遂放心地点头,“那成吧,我陪你去看。”
冬宁支开茯苓,和胡照心挽手上了街,走到桥头口,径直拽着她往昌平街去。
“哎哎哎,你干嘛呢?走错了,牙行往西边呢,这头。”
胡照心带着她就要转方向,却被冬宁死死拉住手,“照心,我想先去趟百戏阁瞧瞧。”
胡照心两眼一瞪,“你还去……”转而一想,又放低了声:“你不会真看上那个戏子了吧?三天两头地想着往那他那儿跑?”
冬宁垂眸摇头,她不敢跟胡照心细说那夜发生的事儿,章凌之的狂怒着实给她吓着了,她便更是惦念起方仕英来,怕给他惹出什么祸事。这才身子稍微好了点,便立马上街来查看。
百戏阁。
昔日张灯结彩的大门此刻空洞洞开着,门口有人攀着爬脚架,将“百戏阁”那大招牌往下取。
“慢点慢点……小心接住咯!”
地面的人伸手去接,不及防被一道娇小的身影蹿进了门。他探头瞧了一眼,没去管,继续托住那沉重的牌匾。
冬宁冲进了馆内,屋子里早已被拆得七零八落,有工人扛着新木在里面穿梭,见着她来,忍不住招呼,“姑娘,让让,别挡道。”
“冬宁,你慢点!我都……都差点没追上……”胡照心终于气喘吁吁赶到,冬宁方才醒过神来,抓着那工人便问:“师傅,劳烦跟您打听一句,这百戏阁是怎么了?”
那人扶住肩上的大木头,却也耐心答她:“嗨,你不知吗?这百戏阁做不下去了,现在被新的东家盘下,准备改个酒楼。”
心底隐隐浮现起不好的猜测,可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般,她抓着他急切追问:“这百戏阁生意向来不错呀,怎会如此?”
“据说啊,我也是听人家在传,说是这里头有个戏子得罪了某位贵人,贵人迁怒,一挥手就把这整个百戏阁都给查封了!”
冬宁恍然失神,双眼逐渐麻木。
胡照心托住她的手臂,却还是不愿相信,只打破砂锅问到底:“你说的那戏子是谁?师傅可知?”
他摇摇头,“嗨,这我哪儿知道去?不过那人也是倒霉,摊上这事儿……你说日后还有哪个戏班子敢收他?哎……”叹着气,他还不忘叮嘱两句:“姑娘们没事就别在里头晃悠了,当心砸着你们。”
周遭的话,冬宁再听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