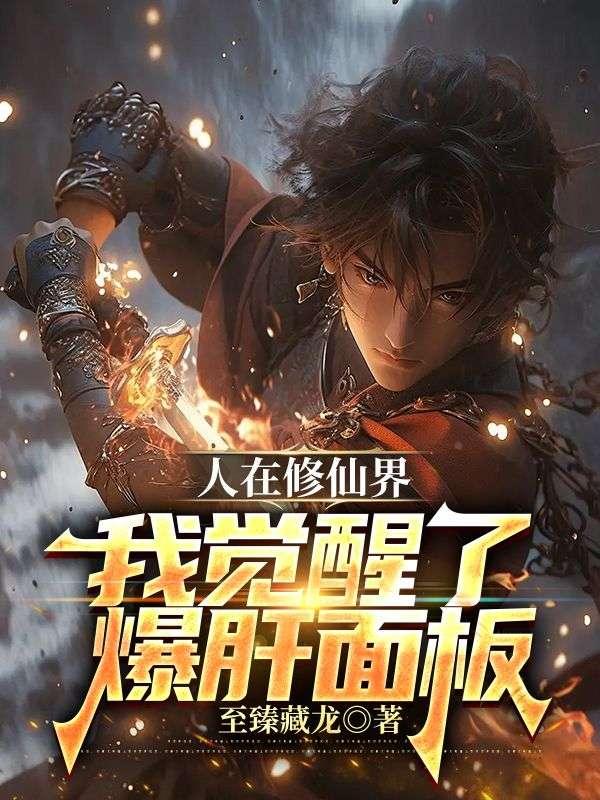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首辅大人的养花守则 > 6070(第14页)
6070(第14页)
薛贞柳上前,牵过女儿的手,“那章越说,说你小时候喜欢他,缠着他,是这样吗?”
冬宁瞬间小脸微红,不好意思地偏了偏头,连芳嬷嬷也是一副有口难言的神情。
只看这主仆二人,薛贞柳便什么都明白过来了。
“章越他个畜生!”
薛贞柳朝地上啐一口。
“阿娘……”冬宁差异地瞪大了眼,眼波颤动。
“您怎么会这么想他呢?”
虽说自己现在埋怨他、记恨他,只想离他远远儿地,可乍一听母亲如此唾骂他,她这么心里摇摇摆摆的,像是空出了一块来似的。
“过去确实是我不懂事……是我对他死缠烂打没错……可那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您犯不着把气都撒他身上呀。”
芳嬷嬷听了,都想连声称是,可也只敢把那话埋肚子里头去。
薛贞柳气不打一处来,手指戳着她的额角,“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到现在还在替他说话,不是鬼迷了心窍去是什么?”骂完,她又看女儿这柔柔弱弱可怜样,哀叹一口气,“不过呢,也不能怪你,毕竟你当时年岁还小,不通人事,猛一下碰到章越这么个心机深重的,也很难不被他骗了去。”
“这要怪呀,还得怪你爹没本事,被贬离了京都。”
冬宁:“???”
听母亲越说越离谱,她实在忍不住,“娘——,您说什么呢?什么叫我是被他骗了去的?他没骗过我……”她咬咬唇,终于,还是把实心话说出来了,“他其实……还是很爱护我的……”
“颜冬宁!我看你真是脑子坏掉了!”她越想越气,脑子已经幻想了一幕幕章凌之诱骗引导少女的画面。可又恨,恨自己在女儿男女意识还未完全明确之时,没能在她身边好好引导。
“傻孩子,你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过来吗?他一个大你这么多岁数的男人,在你十三四岁时就亲你、抱你、摸你……那不叫爱护你、对你好,那叫……侵犯你!”
芳嬷嬷和冬宁同时瞪大了眼。
“阿娘!”
“夫人!”
“行了!”知道她们又要来辩解,薛贞柳现在固执愤怒到什么也听不进去,“颜冬宁,我现在就最后问你一句话。”她嘴巴凑到女儿耳边,小声吹气:“那章越,到底破了你的身子……”
“哎呀娘!”冬宁不耐烦地推开她,“我都说了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您还要问几遍呐?”
“行行行,没有那娘就放心了。”
只要身子还没有破,那过去他对自己女儿做的那些龃龉腌臜事儿,她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让它过去了。
“好了,这事儿咱就揭过不提了,再在章府上暂且对付几日,等你休养好了,咱们就上路,跟娘回山东去!”
夜里,冬宁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合不上眼。
想起白日里母亲对章凌之的误会谩骂,过去她从不曾考虑到过的问题,而今终于漫上心头。
原来若真要和自己在一起,他会引来旁人这样多的异样眼光。可彼时,她从未往这里想过。
不知为何,心里竟泛起股说不上来的滋味。像是青橘腌渍得久了,由酸里都酿出了涩味来。
鬼使神差地,她推开被子,踮着脚,悄悄推开条门缝,溜了出去。
一路溜溜达达,她又站在了燕誉园的书房前。
令她倍感的差异的是,不仅大书房的灯还亮着,连一旁空置已久的小抱厦,竟也亮起了灯。
她看到明瓦窗上投下的影子。
他的影子高大,此刻正立在抱厦内,这么晚了,不知还在那里头做些什么。
就是在这间小抱厦里,有太多她的回忆,他们的回忆。
他为她在墙壁上记录身高,挥着戒尺严厉地教她读书,如师亦如父。
即使他从未有过半步不恰当的越矩之行,可她依旧爱慕上了他。
她在这间小抱厦内躲着写有关于他的艳情小说,甚至还有趁他睡着时,偷偷亲过他的脸……
她故意在背地里造谣,搅黄了和他龚家小姐的婚事,否则而今的话,他孩子说不定都出生了,也不用总被人一直嘲笑是个有毛病的老光棍。
她任性的离家出走差点给他带来大麻烦,可他从未有过半句斥责之语……
他总说,在章凌之这里,颜冬宁可以做一辈子的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