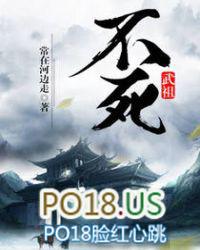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恶魔的游戏——互换人生 > 第2章 二(第8页)
第2章 二(第8页)
剩下的,只有这具沉重的、无法摆脱的躯体,和套在这躯体上、名为“王雅”的、看不见却重若千钧的枷锁。
她得活下去,为了那个躺在医院里、名字也叫李阳的男孩。
她开始在试卷上写下评语,笔迹是王雅的笔迹,语气是王雅的语气。窗外的天,彻底黑透了。
……
又是一天加班。
办公室的灯光惨白,映照着试卷上冰冷的红叉。
李阳(王雅)放下笔,指尖冰凉。
刘老师那声“海拔担当”像根细针,扎在早已麻木的神经末梢。
她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份试卷上,但胸前沉甸甸的重量顽固地提醒着她——这具身体,并非静止的囚笼,而是一座仍在缓慢生长的炼狱。
最初几周,她以为E罩杯已是极限的酷刑。
她学会了挑选支撑力最强的运动内衣,甚至偷偷定制了带有钢骨的特殊款式,试图将那两团沉重的软肉牢牢锁住,减轻对肩背的撕扯。
走路时,她下意识地含胸,试图削弱那过于醒目的曲线带来的视觉冲击和自身的负担。
然而,一种更深层的、持续不断的胀痛感,如同地底缓慢涌动的岩浆,从未真正平息。
某天清晨,她在浴室镜前准备将那头该死的金发盘成最紧实的发髻。
手指滑过锁骨下方时,一种异样的紧绷感让她动作顿住。
她解开紧绷的运动内衣搭扣——那瞬间的释放感几乎让她呻吟出声。
但下一秒,她惊恐地发现,内衣边缘在皮肤上勒出的深红印痕,其覆盖的范围,似乎比记忆里又向外扩展了半指宽。
沉甸甸的坠胀感,也比昨日更加清晰。
“不……”喉咙里滚出一个干涩的气音。
她颤抖着用手掌去丈量、去挤压,试图证明这只是错觉,是内衣过紧的压迫。
但那饱满的弧度,那沉甸甸的手感,都在冷酷地宣告一个事实:F。
一股冰冷的绝望瞬间淹没了她。
她猛地将额头抵在冰凉的瓷砖上,冰冷的触感也无法熄灭胸腔里翻腾的怒火和恐惧。
为什么?
为什么还不停止?!
这具身体难道要无休止地膨胀下去,直到像一颗熟透到即将爆裂的果实吗?
高跟鞋的禁锢已经让她步履维艰,现在连这具躯壳本身都在背叛她,将她推向更深的、无法想象的畸形深渊。
她粗暴地重新扣上内衣,钢圈深深陷入新扩张的柔软边界,带来尖锐的刺痛。
这痛楚奇异地让她清醒了一点。
她看着镜子里那个女人:脸色苍白,金发凌乱,眼中燃烧着困兽般的愤怒和绝望,胸前被勒得更加高耸惊人。
一种巨大的荒诞感攫住了她。
她,李阳,一个曾经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男生,如今竟在为胸围又增大了一个罩杯而恐惧崩溃。
这世界疯了,或者,是她疯了。
生活的每一刻,都变成了与身体持续发育的无声战争。
备课、板书时,胸部的重量无时无刻不拉扯着她的肩颈和脊椎。
她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用手托一下沉重的下缘,或者靠在讲台边,让坚硬的边缘分担一点压力。
这个动作在学生眼中,或许成了“王老师身体不适”或“新习惯”的标志。
她捕捉到一些女生好奇或略带羡慕的目光,也看到个别男生迅速移开视线时脸上闪过的尴尬。
每一次这样的注视,都像鞭子抽在她脆弱的神经上。
生理期成了每月一次的酷刑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