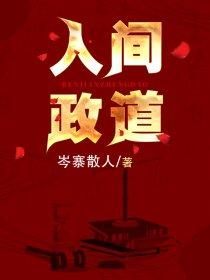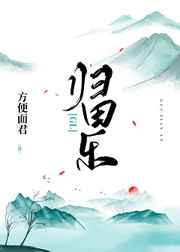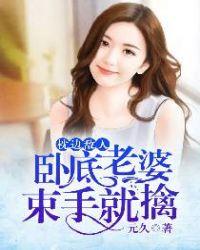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长公主她不装了 > 第 7 章(第3页)
第 7 章(第3页)
乔昭顿时满意的扬了扬小脸。
“既如此,那朕和皇姐决议——开设武举,为国选才!”他站起身,将心中演练好的话一股脑和众臣说出:
“诸位既都赞成强兵护国一策,那便在兵部之下专设‘武选司’,日后春试文举,秋试武举。武举甲第者同进士及第,赐绯袍银鱼,入兵部听用!”
轰——
如一记惊雷炸响,朝堂轰鸣。
”陛下!这、这不合祖制……”
礼部尚书眼前一黑,一把年纪的老臣跌跌撞撞的跑出列。“武人粗鄙,又岂能登堂入室?”
他扑通一声跪下,紧接着,后排官员呜呜泱泱的跪了一大片。
“陛下三思——”
“祖宗之法不可变啊!”
场面一时如沸水泼雪,声浪几乎掀翻太和殿顶部的琉璃瓦。礼部几位老臣跪倒在地,额头磕得金砖咚咚作响。
“朕可是问过诸位异议了!”乔昭头一次被这帮儒生气到:“方才没人提,想必都是赞同朕的!”
那、那怎能一样啊?!
皇帝要于民间招兵买马、操练莽夫,和有意开设武举,让武生位同文臣,全然是两码事!
众文官不敢多言,只是一味跪在地上,以礼制古法为刃,乞求皇帝收回成命。
殿内争执间,忽听前方一道清冷声音响起。
“臣,附议。”
满殿霎时一静。
傅之衍执玉笏出列,背后目光粘灼,却未看向任何人,只朝御座一礼,语气平静,但字字清晰:
“《六韬》有云: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智,则三军大疑。”
“郑大人若忧心武人粗鄙,那更该设武举、明考校——取知兵书、通谋略者为将,而非放任行伍之权落于庸碌之手。”
他表明了支持武举。反对态度最为激烈的礼部尚书一怔愣,不敢置信的看着百官之首的傅之衍。
当朝丞相少年得志,年方十九便随先帝御驾亲征,以一计使五千精兵取得黑石峡大捷,平日里素来克己守礼,群臣敬重,更受年轻一代学子追捧。
丞相的站队,大概率决定了中间派的偏向,如此一来,他这边的局势便不明朗了。
话音未落,新晋翰林院大学士谢临带头跨步出列。
他出身寒门,平日里素来沉默,此刻却脊背笔直:“傅相明鉴!臣幼时居边关,亲眼见突厥屠村——当时若有良将镇守,何至十室九空?”
谢临喉头微哽:“臣深知文人笔墨救不了刀下百姓……如傅相所言,还请陛下开设武举。”
仿佛冰湖乍裂,更多声音接连响起——
“臣附议!”
“臣也附议!”
工部侍郎和尚书右丞相继出列。
“陛下,黄河堤防年年溃,工部正需懂水利的武官督造!”楼佑不顾一边正跪着恳求陛下收回成命的工部尚书,接连上前几步道。
尚书右丞不甘其后:“陇西粮饷多次派发却常年不得落实,也该设个提的动刀的武人监军!”
支持的声音愈发多了起来,他们虽为文臣,凛冽的气势却如新竹破土,齐齐指向同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