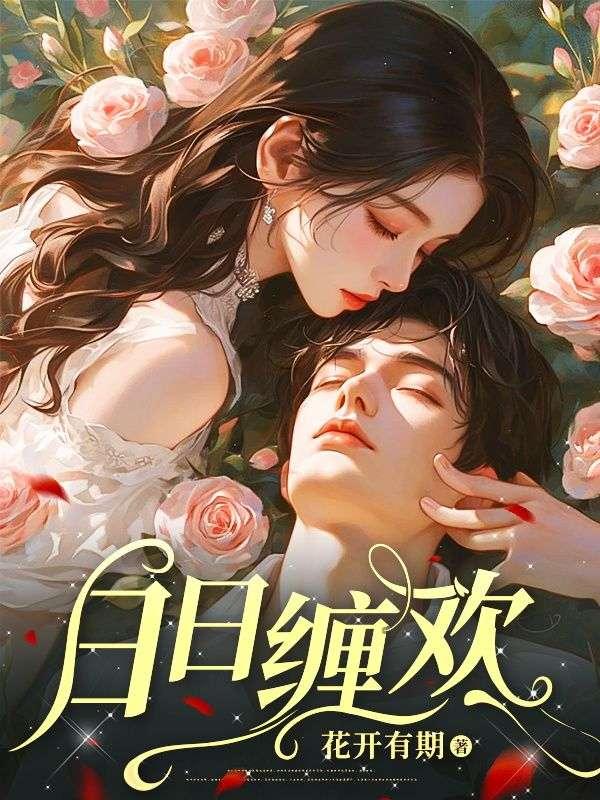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千娇面 > 罗衣相拂(第3页)
罗衣相拂(第3页)
水断栩双手交叠着,玉弯隔着布料,与祝见粼衣袖触碰着,竟比雨落青砖声还响。
处于这一小片天地中,仅有他们二人,鼻息喷洒着,心怦然着。
不知过了多久,终至见到了“青塘苑”三字。
“表兄,到青塘苑了,今日之事,多谢表兄了。”
“无碍,表妹还是快些回屋,勿要着了风寒。”
守门婆子见状,连忙令粗使女使取来油纸伞,除向二位主子问好外,是一句多余之语不敢说。
粗使女使举着油纸伞,将水断栩身子罩住,继而送至垂花门。
几人皆未留意到,祝见粼执握的手,愈加用力,亦垂下眸,应在回味什么。
回至屋中,待沐浴后,水断栩正用棉布裹着鞋履,继而塞入宣纸。
“如此,再阴干,应是不会……不会有损罢。”
“娘子!此等事交与奴婢便好,何须亲自来?”
正自言自语着,谁料玉盘见此情形,急匆匆行至她眼前,絮絮叨叨始。
“你的手才好了些,断不可令你亲力亲为,好了,该歇息了,记住,明日去将刘嬷嬷唤来。”
好说歹说,才将玉盘赶至耳房。
躺于榻上,水断栩脑海中竟挥之不去那抹湖蓝色,疑惑埋在心间,究竟是何人放置暗格中……
“罢了罢了,左右于我无害无利,待阴干后,我再置于暗格处。”
辗转反侧,试图一瞑不视,却仍是睁开双眸,直望着纱幔低垂。
她又念起今日在油纸伞下时,祝见粼面颊潮红。
“究竟为何……怎能面赤至此?好似桃花面。”
转首,望向窗棂,望到日升月落,望到晨光熹微,望到刘嬷嬷进屋轻唤着。
“娘子……您莫非是一夜未眠?”
刘嬷嬷方近床榻,便见榻上之人睁着双眸,眼底略有乌青。
“只醒得早罢了,刘嬷嬷此番前来,所谓何事?”
水断栩起身坐于榻上,心中疑惑着,刘嬷嬷今日倒是怪异,若非要事,缘何东方欲晓时便来?
“娘子竟不知情?可玉盘分明说,是娘子您寻老奴有要事相商。”
“是我糊涂了,”水断栩方才恍然大悟,原是此事,继而开口道,“关乎采买一事,若需牙婆,我这倒有可荐之人,不知刘嬷嬷可愿一见?”
如她所料般,刘嬷嬷面露难色,推搪着不肯应下。
见刘嬷嬷百般推辞,水断栩撇嘴道:“既如此,我亦不强求,只是……妆奁中无故失了好些首饰,劳烦刘嬷嬷将其寻回,我想,相较起来,刘嬷嬷应是比我更为清楚。”
“竟有此事?娘子宽心,老奴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好予娘子个交代。”
见刘嬷嬷信誓旦旦,义正辞严之态,水断栩起身,走至她眼前。
“是了,予我交代,我瞧着,刘嬷嬷您倒更似青塘苑的主子,既然姨母如今已痊愈,我问安时便提上一句,将这青塘苑交与你,如何?”
“扑通!”
话落,刘嬷嬷当即伏于地,口中不断求情着。
“娘子明鉴!老奴并非此心!娘子自然是老奴的主子,老奴绝无二心,亦无逾矩之心呐!”
水断栩见状,俯下身,抬手理着刘嬷嬷发簪。
她将发簪拔出,端详了一会,随着簪子回至青丝的,是声至。
“那便按我所说,用我所荐的牙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