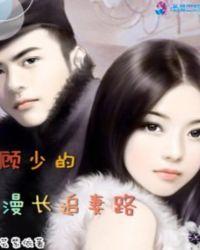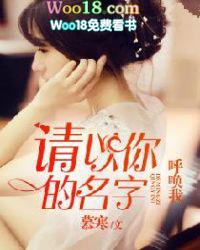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探花郎的极品二嫂 > 第三章(第1页)
第三章(第1页)
洗三这日,天还没亮,孟青的娘和弟弟就提着包袱拎着鸡笼前往渡口等船,孟父没去,他要去瑞光寺下的纸马店守门做生意。孟青的大伯在瑞光寺做和尚,托他的福,瑞光寺寺内诵经超度用的祭品大部分由孟家纸马店供应,孟父日日要剪纸钱做香烛,离不了家。
天不亮出门,日上三竿,孟母和孟春乘船抵达杜家湾渡口。
春日春水泛滥,河水漫过河边的石阶,孟春脱下布鞋,赤脚背着他娘上岸,再返回船上拿包袱提鸡笼。
孟母站在岸上往远处眺望,目之所及皆是牵牛扶犁在水田里耕田的农人,她念叨说:“你姐坐月子撞上春耕,农忙无闲人,她婆母估计照顾不周,你姐要吃苦了。”
孟春放下鸡笼,他擦擦脚穿上鞋,说:“杜家从我姐手里拿走一百二十贯钱,抵得上他家三四年的收成,他们敢亏待她?”
孟母扯了扯嘴角,说:“就怕杜家看不上,通圜坊余记米行的东家可是愿意出三百贯的嫁妆要把他二女儿嫁到杜家,你姐的一百二十贯跟三百贯一比,可就不够看了。”
“余二娘哪比得上我姐,我姐可不输官家小姐。”孟春比孟青小三岁,是跟在她屁股后面长大的,最是信服她,在他眼里,孟青哪哪都好。
孟母知道小儿子的德性,她不跟他犟,提起一个包袱进村。
孟春扛起鸡笼忙跟上。
杜母坐在剁鸡草的青石板上拔鸡毛,老远就看见朝她家走来的两个人,直到人走到跟前,她才抬头怠声招呼:“亲家来了啊,来得挺早,天没亮就出门的?”
“对,赶早不赶晚。”孟母发现杜母一直盯着她的衣裳瞧,她纳闷地低头看看,衣裳上也没啥异样。
“亲家母,你身上的长褂是靛青色?”杜母瞬间变脸,她嗖的一下站起来,扬着脖子盛气凌人地质问:“你咋能穿这个色?唐律规定了,商人属杂类,跟部曲、奴婢等同,只能穿黑、白、褐黄三种颜色。你是商人妇,只能穿这三个色。”
商人妇……孟母被挤兑得满脸通红,她扯了扯衣角,强笑着辩驳:“城里很多商人都穿这个色的衣裳,没人管的。”
“话不能这么说,你我两家要是没对亲家,我管你穿什么色,你就是穿红披紫我都没意见。可我家有个读书人,我小儿子以后是要做官的,你们要规矩点,可不能影响到他。”杜母趾高气昂地说。
一旁的孟春冷笑一声,他想起三天前杜悯去他家纸马店探听丧葬行业的事,话里的机锋明晃晃的暴露在太阳下。他讥讽道:“大娘,话可别说太早,你小儿子能不能考中还两说。”
“孟春,闭嘴!”孟母横过去一眼,眼风掠过杜母,她气得像头驴子一样鼓着大鼻孔瞪人,可见是戳到痛处了。
“亲家母,苏州离长安甚远,圣人管不了这么远。唐律是唐律,但有句话叫法不责众,城里商人都这么穿,官府是不会责罚的。你别太害怕,没事的。”孟母考虑到两家是姻亲,她女儿是杜家媳妇,和气地解释。
杜母不依不饶:“反正你不能穿这个色的衣裳来我家,你想穿就关起门在你自己家里穿。”
孟母脸上的笑绷不住了,她呛声道:“杜悯是你儿子不是我儿子,更不是我女婿,我就是出事也连累不到他,你约束好自己就行了。”
杜母气得脸色发黑。
孟母也气得够呛,不过她是商人妇,跟人打交道多,练出了功夫,再气也不甩脸子,她假笑道:“亲家母,你忙着,我去看看青娘和孩子。孟春,跟上。”
孟春憋了一肚子气还不能发,他动作粗鲁地拎起鸡笼,鸡笼里的鸡颠得拍翅膀挣扎,飞出来的碎羽扑杜母一脸。
“小瘪犊子。”杜母呸一声,她气得胸脯剧烈起伏,见那不懂规矩的母子俩大摇大摆进她的家,她气得抓起盆里的鸡狠狠砸在地上,“吃吃吃,吃屎去吧!商人果然低贱,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孟母听到这话气得要吐血,偏偏只能当做没听见,商人地位低,被瞧不起是常有的事。她拽住孟春,低声说:“随她骂,骂完还是要给我们做饭吃。”
随后又嘱咐:“这事别跟你姐说,她还在坐月子,受不得气。”
孟春深吸两口气,他装不出高兴的样子,便放弃道:“算了,我先不进去了,我出去转转,看我姐夫在哪儿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