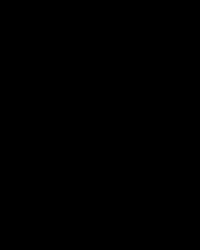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重回灾年给老妈完美童年[七零] > 第 20 章(第1页)
第 20 章(第1页)
方文静陪着晓芹,揣着那张薄薄的孕检单,踏着暮色,回到了她和成刚的家。
成刚正佝偻着背坐在门槛上,手里笨拙地修补着一个豁了口的破箩筐。竹篾刺着他的手,他也浑然不觉。听见脚步声,他猛地抬头,见是晓芹回来,整个人弹了起来,沾满竹篾屑的手在裤子上擦了又擦,眼神慌乱,手脚一时竟不知该往哪搁。
当他的目光触及晓芹微微苍白的脸颊,又看到她下意识护住小腹的动作时,他彻底僵住了。
空气仿佛凝固,只剩下他粗重的呼吸声。
方文静无声地将那张孕检单递到他面前。
成刚伸出粗糙颤抖的手接过,那纸轻飘飘的,却似有千斤重。他看看纸,又猛地抬头看看晓芹,再转向方文静,嘴唇哆嗦得像风中的枯叶。
他“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晓芹脚前,脸深深埋进她洗得发白的旧衣襟里,嚎啕声撕心裂肺:
“晓芹!我。。。。。。我混账!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啊!我。。。。。。我有孩子了?我要当爹了?!”他抬起头,脸上涕泪纵横,“我改!我一定改!我对天发誓!往后我要是再碰你一指头,再沾一滴猫尿,就让我天打五雷轰!让我这条腿也彻底烂掉!我好好下地,我卖力气!我。。。。。。我好好待你!咱俩。。。。。。咱俩好好过!把这娃拉扯成人!晓芹。。。。。。求求你。。。。。。你再信我一回!就一回!”
晓芹望着脚下这个痛哭流涕、赌咒发誓的丈夫,再感受着腹中悄然孕育的小生命,一直强忍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决堤。她泣不成声,只是伸出手,颤抖地抚上成刚那沾着泥土和草屑的、乱糟糟的头发,用力地、用力地点着头。
方文静默默站在一旁。暮色四合,沉甸甸地笼罩着村庄,家家户户的烟囱升起袅袅炊烟,空气中弥漫着泥土、柴草燃烧和饭菜混合的独特气息。她深深吸了一口这熟悉又沉重的空气,挺直了单薄的脊背,转身,朝着自己家那点昏黄的灯火走去。
时光如村口那条小河,静静流淌。一个冬天在积肥备耕、修补农具、守着炭盆纳鞋底、围着火塘剥花生、顶着寒风挖地窖储冬菜中悄然滑过。转眼,冰雪消融,村里最年轻的妇女主任方文静,攒着恢复高考后积攒的勇气与知识,即将踏上那决定命运的考场。
揣着全家从牙缝里省出来、东拼西凑的几块钱路费和一小包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在方夏荷既忧心忡忡又满怀期盼、何田充满崇拜与向往的目光注视下,方文静独自踏上了去县城的路。
考场肃穆,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如同密集的春雨敲打窗棂。她感觉自己像一条在干涸河床上挣扎了太久的鱼,终于奋力一跃,重新游回了那魂牵梦萦的知识的河流。
题目艰深,但她咬紧牙关,凭着在田间地头间隙、在无数个煤油灯熏黑灯罩的夜晚反复咀嚼、融进骨血的知识,一字一句,将希望倾泻在雪白的答卷上。
放榜那天,方文静没有去县城。她像往常一样,天蒙蒙亮就扛着锄头下了地,汗水很快浸透了背后打满补丁的粗布衫。心,却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在胸膛里“砰砰”地擂着鼓,几乎要撞出来。
日头快爬到头顶时,村支书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老永久”,风风火火地冲到了方家那低矮的院门口,人还没站稳,手里就高高扬起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纸,洪亮的嗓门因为激动而劈了叉:
“文静!文静丫头!好样的!考上了!省城师范大学!金榜题名了!通知书来啦!”
这消息如同平地一声炸雷,瞬间在方家小院和整个正阳村掀起了滔天巨浪。方夏荷第一个从灶房里冲出来,一把抢过通知书:“考上了!真考上了!出息了!”
王君正背坐在门槛上,眼里也泛起了泪花:“好!好啊!念书好!光宗耀祖啊!”
何田更是兴奋得小脸通红,像只小喜鹊似的围着方文静又蹦又跳:“小姨!小姨!我就知道你能行!你是大学生了!以后是城里的大学生了!”
小小的院子里,被巨大的、纯粹的喜悦淹没。
村里人闻讯纷纷赶来,很快挤满了方家的小院。羡慕的、惊讶的、真心实意道贺的、还有那酸溜溜嚼舌根的。。。。。。各种目光像针一样交织在方文静身上。
她站在院子中央,手里紧紧攥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钧的录取通知书,脸上那片“火烧云”在众人聚焦下似乎又灼热起来。但这一次,心底翻涌的不再是自卑的刺痛,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极其复杂的洪流——激动、酸楚、扬眉吐气的微光,还有那沉甸甸压下来的、对未知前程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