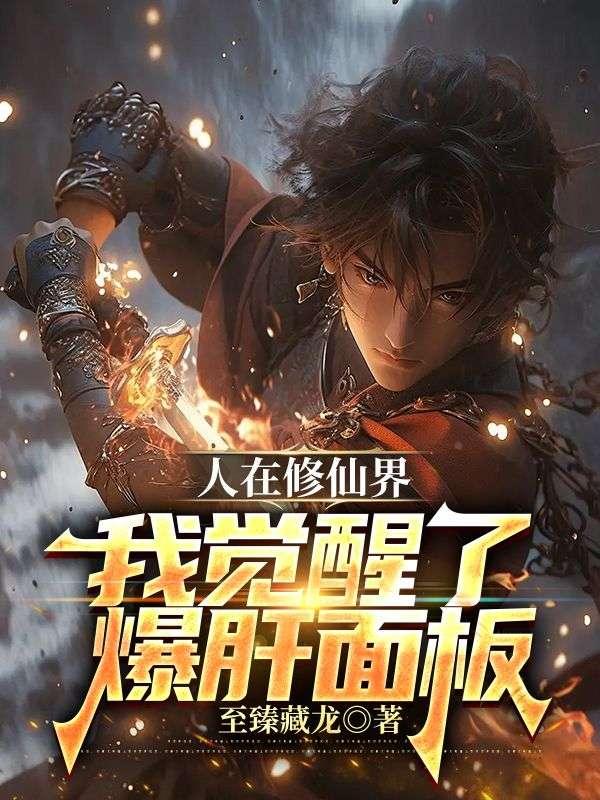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折旋结 > 第 5 章(第3页)
第 5 章(第3页)
放任罪大恶极之人去说风凉话,引申为没有天理。
一个昼夜纸若飞雪笔走龙蛇,两餐的果点香气与笔墨芳馨融汇一处难舍难分。尽管艰涩的经文早已烂熟于胸,学以致用到几何则全凭个人修为了。
是了,师父是谁?她的那点心思伎俩又何须解释。师父气的从来都不是独辟蹊径而是肆无忌惮,怪的也绝非剑走偏锋只因胆大妄为。
与之相较,好吃懒做天资愚钝在某种程度上甚至都要更为稳妥些。毕竟,在风惊幔这样的年纪,代价是一个过于虚渺又空幻的词。
因为懂得,才截住了殷桑的话。
她也知道什么叫后怕。就像那朵被她自作主张干掉了的星斐花……
算了算了不去想了。风惊幔觉得,若是讨了师父一顿骂或许还能好过些。偏偏挨罚的是殷桑这厮,呛的又是他老人家,果然冲动的事不能做。
“快别写了,我们出去玩儿啊。”三个小伙伴兴冲冲的跑来找她。
“冲动是梦魇。”风惊幔一遍一遍抄写着《朔心决》眼皮都没抬一下。
“这家伙什么时候开始转性啦?”
风惊幔:“你是梦魇。”
“梦魇都转性了你居然不好奇?”
风惊幔:“你转了什么性?”
当得知宫城噩梦已除,师父已向君上请了旨晚些时候即可出宫时,风惊幔有点相信梦魇转了性或许是真的。
不然呢?筑几个所谓美梦这种但求无过的做法若能成事她打死都不信。
不是我们将其战胜,而是被其放过了。幸运而已,也没什么值得说的。匆忙间还没忘给秦恭俭留了张字条辞行:有事托梦。
入夜多时。
此刻,再要紧的事也爬不回梦里去听了。
宽阔的街市商贾云集高声争闻,远远望去恰火树银花类兰缸如昼。如练的月色不小心沾染了人间烟火,流转于繁华里堪堪晃瞎了一众鸟眼。哪里还会舍得去睡觉。
一排暗纹云头靴踏在瓦片上不时伴有节奏般的轻摆着,下方是那条悬灯结彩又流动着的光带。几个人头枕着手臂仰面躺在不知哪家酒楼的屋顶上,晚风知趣地捎来阵阵浓郁甘冽的酒香。
衍城的夜街再美,他们也不会为此景致便晃瞎了眼这般没出息。浸染了烟火之气的,是头顶上空俯瞰尘寰间或回旋飞翔着的还鹰。
不记得是谁想出了这么好的角度,赦免了脖子的同时又拉近了与战神的距离。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身下的瓦片好硌吗?”
“这里不是祜城,没有那么多的鸟喜欢睡屋顶的。”殷桑答道。
迦蔗果轻叹了一声,小心的侧了侧身体。望见旁边的殷檀面色有些凝重,遂问道:“你这是怎么了?有心事?”
“还鹰的巡视和警戒通常不会这般密集,我总觉得像有事情要发生。”殷檀咬了咬唇,闪动着眼睛若有所思,突然道:“惊幔,你——”
但见风惊幔两脚交叠身姿舒展,整张脸却已睡得软沓沓的,稚气如婴孩。七师兄的魅力竟然不足以支撑起这花痴的眼皮。
“嗯,说的对。”
“喂喂,这家伙居然说梦话了嘿。”
“就不能是被酒气熏到说胡话了吗?”风惊幔突然伸开手臂摇晃了下脑袋,“除了酒楼就没有别的楼了吗,我被熏得都要吐了,醉死之前咱能不能换个地儿?”
忘了这个茬儿。
酒气之于风惊幔,闻之上头,饮如鸩毒。平日里若未掉进酒缸酒窖醉死还不至于,想是此间的佳酿过于幽郁醇厚了。良心店家。
“酒香都叫你闻了去了,人家还怎么做生意,再不走怕要收钱了。闪了闪了。”殷桑坐起了身,拍了拍同伴准备撤。
风惊幔一把拉住迦蔗果的袖子,表情痛苦地道:“扶我一下快,硌死了。”
“不要。偏你吃的多还不长肉,活该你硌死。哼!”
唉呀这死丫头,嘴皮子什么时候这么溜了,都是叫殷桑给带坏的。风惊幔也不是矫情,只是方才想事情出了神,身体撂在瓦片上半晌一动未动戳得麻了。
方才的那句“说的对”是回应殷檀的,她也觉得有事要发生。不过,仅是换身衣服怕是不够,看当下的时辰,洗个澡再动手差不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