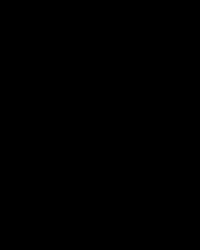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和死对头约法三章后再成婚 > 第 17 章(第1页)
第 17 章(第1页)
及至半夜,月华倾泻,一室岑寂,偶有微风穿廊而过,发出簌簌呜咽。
程陵虽双眸轻阖作休憩状,耳尖始终向着门扉方向,时刻注意着门口动静。
卧榻许久,他的意识逐渐松散,昏昏沉沉将眠未眠之际,耳畔终听见门轴转动的吱呀轻响。
程陵骤然睁眼,眼睁睁见着贺珏那一袭素色衣衫迈过门槛,他当即掀被而起,悄无声息地追了出去。
他尾随那道飘忽身影,一路直至后园,贺珏忽而驻足,立在几树海棠之下。
程陵眼见她徘徊许久,选定一个位置后倏然蹲下,开始在丛丛夜草中扒拉翻找起来。
自城外白龙寺归来已过三日,贺珏每至更深必起,他亦悄然尾随她三夜。
这些时日,他与贺靖遣人遍寻城内城外,连许绒的半点踪迹都未寻得。
程陵疑心她已经离京远去,又修书数封,快马送至京畿各州故交处,托他们帮忙关注一二。
贺珏不欲惊动旁人,连贴身侍女也不愿带上,他二人日日早出晚归,将许绒可能栖身之所一一寻遍。
一日未寻到人,贺珏便一日不得安枕,每至夜半必起身至园中掘草,自己却浑然未觉异样。
程陵始终未点破,又担心生出差池,只得每日夜半时分悄然随行,在她身后守着。
他总是待在她数步之外,默然观望。
此刻他眼前的贺珏,一头青丝逶迤及地,发尾皆垂落在泥地绿草中,素衣墨发交织的画面,显出几分说不出的诡谲。
然浅淡月光打下来,在她面上泛开朦胧光晕。
程陵所处的位置,恰能望见她浸在清辉中的半边侧颜,恍若谪仙临世,竟又于诡艳中透出几分超脱世俗的安宁静谧。
几道海棠墨影东移,忽又消失不见,乌云遮月。
贺珏终于起身,手中仍攥着乱蓬蓬几茎怪草,飘忽忽折返回院。
近来暑气渐盛,空气干燥,入夜仍闷热难消,今夜更是热得非常。
阿愿辗转反侧难以完全入睡,决定索性起身至院中透口气,起身时才发觉后背的中衣被汗浸透了。
她揉着惺忪睡眼,哈欠连天地步入院中,待行近主屋前,忽注意到主屋房门大敞,阿愿眉头一跳,疾步冲入屋中。
目光先扫向贺珏床榻,榻上空空,再转向程陵那侧,竟也无人在榻。
阿愿慌忙转身欲出院寻人,却远远瞧见贺珏的清癯身影,自院门外徐徐入内。
阿愿小跑上前,一边颤声呼道:“小姐,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了?吓惨我了!”
贺珏未作声,好似恍若未闻。
“小姐?”阿愿又走近几步,凑到她面前唤道。
“阿愿。”一道清冽嗓音蓦然响起,阿愿循声向后望去,见程陵不知何时已进了院中。
程陵抬起右手,修长食指轻抵唇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阿愿当即屏息,这才凝神细看贺珏。
却见自家小姐双目空洞,面上竟无半分生气,同记忆中令自己惊吓到的那张面容渐渐重合。
阿愿心中一紧,她的小姐这般情状,是又梦游了?
贺珏这副模样,她已许多年不曾见到了,上一次如此,还是国公夫人重病在榻之时。
阿愿怔楞间,贺珏已飘然向前走出数十步,上了台阶,跨步进了屋。
程陵走到她跟前,,挥了挥手,示意阿愿退下,阿愿默不作声退开几步,程陵又忽地轻声唤住她:“打盆水进来。”
程陵进屋时,贺珏已如常一般卧回榻上,气息匀长,俨然熟睡多时的模样。
她原攥在手中那把青草零落在榻边,程陵伏身将那些草一一收束起来,他询问过郎中才知,贺珏每夜去挖回来的这些,尽是些宁神静气的草药,草木幽香浮动,同她身上的清冽气味如出一辙。
阿愿打了水进来,程陵示意她放下便退,她满腹狐疑,却仍依言行事退出房门。
在转身阖门之际,阿愿瞥见程陵一手拿着干净绢帕,一手执起贺珏的手腕。
阿愿唯恐房中人还有吩咐,在门外静立片刻,这须臾之间,脑中已回想起三日前的晨间,在廊下被程陵唤住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