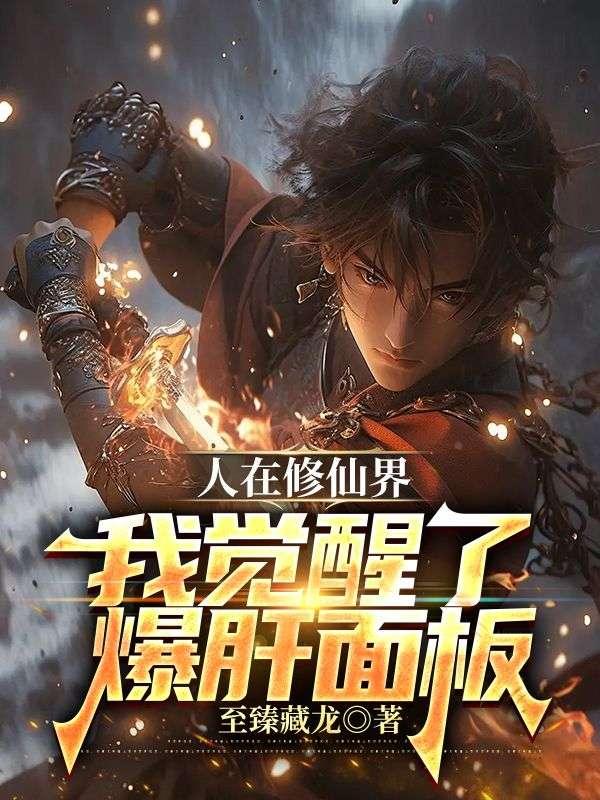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假死后病娇世子为我守节 > 饲养疯狗的第八天(第1页)
饲养疯狗的第八天(第1页)
却不想,只是又一个新的火坑。
郁松接他回家,是因为他的宝贝儿子郁安中了幻毒。又不知从何处寻的医师,说虽无药可解,但能以至亲行换血秘术。郁松这才想起郁净之这个流落在外十数年的骨血。
于是郁净之以私生子的名头回了京,郁净之取代郁安成了世子,郁净之成了整个国公府“待遇最好”的人。
他被推回屋子里,就放了竹影出去。
不声不响地拿起先前没绣完的纹样,继续绣了起来。
一针一线,仔细绣着。其实郁净之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娘教过他刺绣,他绣得很好、很好。阿娘说过,她的阿濯是天底下最聪慧的好孩子。
只是后来,他娘死了,郁净之就再也没绣过什么东西。又为了给赵绥宁绣嫁衣重新拾起,一边绣着,一边失神地把绣花针戳进皮肉里,周而复始。
·
赵绥宁现在很不好。
某种湿哒哒的恶心液体沾满她的外衣,黏在皮肤上。头下是软软的黑色的泥土。
夜深,她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总之不是在国公府。
一个时辰前,小厮跑到了她的院子,递了张纸条说关于谷彤的病症,公主还有别的想问,约她去府上细聊。
她一收到消息就匆忙赶出去,提着灯走在空荡的街道上,没想到就倒霉地被人绑了。
赵绥宁十分奇怪,她一届小小医师,也没治出过人命,也没得罪过谁,况且她已经易了容,和从前相貌只有三四分相似,不仔细想根本认不太出来。
难道是郁净之得罪人了,那人寻不到他的仇就来寻自己报复?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她叹气,后悔自己太过轻率。
双手有明显的束缚感,眼睛也被遮住,手法还挺专业的。不知道香囊里还在不在……如果没被绑匪摘下的话,她或许还有机会反抗。
“咕噜咕噜”的车辙声响起,又很快消失。然后是脚步声,有些杂乱,对面起码有五个人,赵绥宁皱眉。
今天她不会折在这里吧。
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近。
有什么东西轻轻覆在她面上,湿湿的,像是沾了水的纱巾?还是宣纸?
一层又一层。
鼻息被挡住,却又能透出一点,吸进一点,这是极大的折磨,赵绥宁不得不更努力地呼吸才能维持正常状况。
很难受。
密密麻麻的汗珠迅速在她鬓间聚集,却迟迟不落下。
她隐约听到身边有人在说话,不远不近的距离。
“你要做……”是轻却沙哑的女声。
接着男人的声音响起:“若不是她……”
“我们的事……毁……”
赵绥宁再无法专注地去听那对男女的交谈了。放在她脸上的东西越来越多,越重,水液浸湿的层状物带来被缠绕般的窒息感。
快呼吸不过来了。
不行。
赵绥宁挣扎着像活鱼一样翻滚起来,试图把脸转着让层状物掉落。
阻隔感终于剥离,她大口大口呼吸喘着气,渴求着空气。
久违的接近死亡的感觉,她磨着后牙,嘴唇紧抿。
沉重的一脚落到她身上,赵绥宁闷哼一声蜷起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