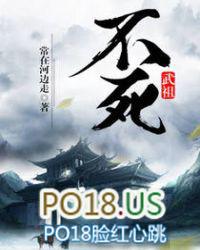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非要攻略死对头吗 > 攻略目标(第1页)
攻略目标(第1页)
倾泻的灿日氤氲成朦胧金雾,春寒散于临窗翠枝。
雕花阁门缓缓合上,日色减退,残留暖意尽数洒在秦津那身绣金鹤纹朱红锦袍上,鲜艳的服饰并未喧宾夺主,反倒衬他眉眼清绝矜贵,更添几分疏狂的风流意气。
身形劲拔,他的这副皮囊极为出色,又因出生在金玉堆里,清贵无双的气度浑然天成,皎如玉树,便是在这遍地富贵的长安城内也显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御安长公主反应过来。
毕竟这天底下敢无视她的命令,不经通传便闯入的人屈指可数。
只是尚且来不及露出喜色,御安长公主便被秦津那句轻描淡写的话震得瞪目哆口,耳畔嗡嗡作响,结舌许久方才憋出一句哆哆嗦嗦的话:“你是说上元节那日,你、你与二娘相约姻缘树下?”
荒唐。
简直荒唐。
但凡久居长安,何人不知二人恩怨,那可是能追溯至先帝在世时,两人尚在呀呀学语之时。长达十几年的明争暗斗,早已是水火不容的两人交锋尖锐,难以共存。
这两人相约姻缘树下,无疑比青天白日见鬼还要骇人听闻。
蒋施彦只觉可笑至极,按捺不住要出声质疑,只是嘴刚张开,便忽而听到薛溶月开口,声音冷漠含霜:“那日,我确实是去寻他的。”
蒋施彦不信:“你去寻他作甚?”
御安长公主凭借对二人的了解,小心翼翼问:“互砍吗?”
秦津懒散地抬起眼,锐利的眸光比寒潭幽深,与薛溶月毫不掩饰的目光相对。
两道目光不偏不倚,平冷直抒地碰撞在一起,在无形中化成两条盯上猎物的毒蛇。
迎着薛溶月的目光,秦津剑眉微挑,薄唇轻扬,对她勾出一道恰到好处的弧度。
一抹在外人眼中平易随和的笑容,好似不夹杂任何恶意。但薛溶月与秦津斗了十几年,早已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她很清楚,秦津是在挑衅她。
强忍愤怒移开目光,薛溶月维持面色如常,转过身子,语气平静地回御安长公主:“是啊,去杀他。”
徐氏与蒋施彦未曾料到薛溶月言辞会如此直白,更惊讶于两人之间的恩怨已经如此激烈,一时不敢再开口言语。
“还真是啊。”唯有御安长公主一手扶额,早有预料,见两人斗得跟乌鸡眼似的只觉头疼厉害,不由叹气,“怎么又闹成这样了?”
纵使两人这些年斗得不可开交,但早已不是稚童,很少会再将“我要杀他”这种话挂在嘴边,平白给对方落下话柄。
也不知这是又发生了什么事。
秦津恍若未闻,薛溶月也没有开口。
无奈叹气,御安长公主问秦津:“那你今日来,是特意来为二娘作证?”
这话说出口,御安长公主自己都觉得可笑,果不其然,话音刚落,秦津与薛溶月一同笑出了声。
两人相视一眼,一个冷笑,一个嗤笑,又颇觉相看两厌,一同敛起笑。
御安长公主:“。。。。。。”
胡商画出了道童长相,在迈进阁内那一刻,秦津便发现人已经被五花大绑绑起来了,便不欲在此时多言。
懒洋洋地拿起一块白乳糕,秦津非常坦诚:“一来谢薛娘子那日不杀之恩,二来自然是瞧热闹,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