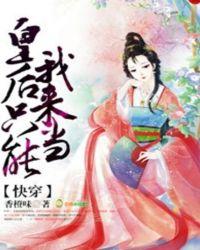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洛阳养狗记(重生) > 第 7 章(第3页)
第 7 章(第3页)
荀郁听长公主点的那几个皆是崇有尚实之人,便知长公主确实在好意指点她。
时下贵“无”,从老庄放达自然之说。众名士镇日挥麈谈玄,言辞虽妙,却如虚舟飘瓦,于事无补。在这些人之中,却也有些关心国家治乱,言行有物之人,前头所提几人便是这般。
荀郁前世执政日久,越发对那些清谈误国之人不屑一顾。被那些既不成事又没主意的“名士”倒足了胃口,她才越发珍惜可用之人,想必长公主也深有同感。
荀郁知道,这几个通才硕学之人恐怕便是荀煦精心安排的,而那些只会“谈玄说妙”的,就不知世家们插了多少手了。
这当中只那裴维,却是长公主从河东裴氏中提上来的一个旁支子弟。裴维因不同大流、尊崇儒术而迟迟不见出头,长公主觉着此人可用,此番便是为他攒资历的同时,也在太子身边放了自己的暗桩。
只不知,长公主让她去,又是出于何等考量。
不论如何,出奇顺利地得了长公主首肯,这番近水楼台的机会便被她握住了。
荀郁松了口气,便又暗暗思索起后头的行事来。
只是拦下王澄之事显然不足,何况此事无人知晓,于她又有何益?
那“神不知鬼不觉”的,若做的是坏事,只会叫人窃喜;若是好事,反倒叫人苦毒钻心。
她还得想个法子,让太子意识到长公主在此事中的动作和意图才行。
纵然她可以直接告诉太子,再给他出主意,叫他防备长公主。
然若如此,一来被长公主察觉的可能性很高,二来,且不说太子会不会就信了她,以他惯于及时行乐的性子,便是知道王七与自己如何受的罪,怕也不会积极应对,只避事罢了。
她得逼迫司马丹行动。
如此暗下决心不提,另一头却也有事发生。
因司马丹还要去找几位世家子弟叙旧,便未同回,因此荀郁也就不知,在她走后不久,荀煦从一灯树后踏出,唤住了司马丹。
“臣中书令荀煦见过太子。”
虽未曾与荀煦交游,并不熟知其人,司马丹多少也见过她几次,略有几分敬重:“荀令君?今日欢庆,不必多礼。之后还要劳烦令君指点教诲,到时孤再向令君正式拜礼。”
荀煦再揖,随后看向荀郁离去的方向,道:“虽恐逾越,下官却有一问。”
司马丹下意识随她看过去一眼,心道小丫头回去与长公主不知又是什么情形,又立马回神,神情疑惑地看着荀煦。
荀煦没卖关子:“不知太子对武陵长公主殿下有何见解?”
“大姑姑?自然是……很厉害了。”
“长公主实有经国之才,内治国政,外主兵伐,皆运筹帷幄之中。”荀煦赞同司马丹的意见,“然而殿下所见,仅仅如此?”
因了荀煦在朝上请东宫就学之事,司马丹对此人也隐隐有些想法,闻言笑道:“不知令君此问,是在问孤对亲姑姑的看法,还是对‘政敌’的看法?”
这“政敌”二字一出,荀煦便知司马丹对情势尚有几分知觉,心中略略安定。
“既然殿下清楚,便该有所防范才是……依殿下所见,这丹阳郡君又是如何?”
“好郎君,孤尚未拜师,怎的就考校起来了?”
“还望见谅,只是殿下知晓,可以这般交谈的机会并不多。”
这倒是,平日他身边宫人耳目等众多,往后讲学更是明面出入,随便什么话都有耳报神送到公主府去。
“孤知道令君何意。只是令君有所不知,丹阳与大姑姑的关系却是有些复杂的。现下她只是孤的妹妹罢了,若是令君另有见解……”司马丹又笑,“只怕您还没有那个资格。”
想了想,他又补充道:“孤不喜那弯弯绕绕的,好叫令君知道,若想将宝押在孤身上,令君怕是选错了人。”
荀煦蹙眉。
司马丹看着荀煦的脸若有所思,突然道:“说来……听闻令君曾有一妻室,敢问尊夫人姓氏?”
闻听此问,荀煦眉头解开,面如静潭,无声地望着司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