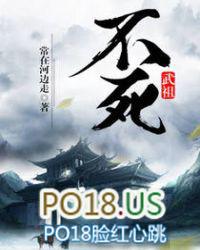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执意惹春烦 > 初遇一(第1页)
初遇一(第1页)
阿发瘫坐在地上,干裂的上唇磕着下牙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林枝意听不清,不过无外乎是些忏悔之言。
他身旁的齐默凡大抵也是看多了见惯了这场面,面无表情地将他从泥地上拽起。
他审视着阿发的表情,质问道:“前日亥时,你人在何处?”
阿发被他猛地拽起,身子还有些发软,他舔了舔唇角,半响才嗓音沙哑地开口:“小的这几日都在。。。广源县!”
齐默凡瞧着他满是泥渍的裤脚,确实像是刚从外面赶回来的样子,继续追问道:“就这么碰巧不在家!?”
阿发答道:“我跟我爹大吵一架,他让我滚,我就先走了。”
齐默凡道:“吵架原因?”一旁的书吏也盯着阿发,手中毛笔不停记录着。
阿发接着道:“我爹他嗜酒成性,年前郎中刚告诫他戒酒保命,我以为他这回定是听了,谁知道几日前又被我撞见他在酒楼,我想着先拉他回家,他非是不肯,还扬言要打死我这个不孝的!”
齐默凡手一松,他整个人踉跄了几步,撑到一旁的桌角才勉强站稳,他眼角快速扫了眼角落的空酒坛,又忙垂下脑袋。
齐默凡问道:“平常这院子只有你们父子俩居住吗?”
阿发答道:“我不住这,我跟娘子住在她娘家。。。”他的声音没有刚才那般激动,似是有些羞愧。
齐默凡微蹙着眉头道:“那为何不回家,跑外地去了?”
阿发低着头,断断续续地说道:“我同窗方岚在广源县我找他去了,他能为我作证,我怎么可能杀我爹呢!”
一旁的林枝意将尸身手臂缓缓放下,齐默凡侧身留意到她准备脱手套的动作,上前询问道:“林郎中,如何了?”
林枝意一边写着验状一边答道:“我用银针三探其口内,未见青黑,死者的舌下络脉也无中毒之症,可以初步排除毒杀的可能。”话落,她指尖指向尸体胀满的腹部。
她道:“他真正的死因应该是死于肝脉解索引发的败症,至于缘由有些人是因为饮酒过量所致有些是。。。”
林枝意心中虽有别的怀疑,但见尸身口内、身侧皆无异常,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她此刻参与查验,不过也就是为了查看林家血案文书,娘亲当年就是因那水疫招来杀身之祸,若是我再重蹈覆辙,不仅这么多年等待付诸东流,还可能会给璇玑阁众人带来杀身之祸。
“如此,便是病亡了,这肝脉之症八成是与他饮酒不节相关。”齐默凡垂眸盯着地上的空酒坛,心下有了判断。
阿发微微抬眉瞧了眼众人,声音发颤地哭道:“我就知道!叫他少喝点酒,他就是不听,如今落得这般。。。”
齐默凡斜睨了他一眼,正了正自己的乌皮腰带,缓缓开口道:“天色也不早了,明早你书信一封,叫你那好友来衙门一趟,日后也好有个旁证来证明你的清白。”
说罢他又冲着小捕快使了使眼色,小捕快立马心领神会,转身去吩咐院中其他的差吏:“你们也手脚麻利些,记录完便将尸体运回衙门的停尸房吧。”
“齐捕头,上回的报酬。。。”林枝意刚准备轻声讨要个说法,齐默凡用眼神示意她周围还有旁人。
她有些不满的看着齐默凡,那人倒是一脸气定神闲地沉声道:“齐某自是言出必践,只是还未到时候。”
林枝意冷笑调侃道:“看来还得挑个良辰吉日呢!”
她收拾完器具拎着木箱,站在来时的马车旁,皮靴碾着脚下的小树果。
小捕头从远处跑来,朝她抛来一粗布囊袋,颠了颠里面有碎银几两,这便是林枝意今日的工钱,小捕快说:“走吧,头儿让我送你回去。”
马车缓缓停在璇玑阁后巷,林枝意轻松地从马凳上一跃而下,跟小捕快招呼了声,就朝暗色里走去。
与前街热闹的景象不同,后巷里静悄悄的,虽能依稀听见前街酒客们举杯畅饮之声,但林枝意还是打了个冷颤。
再往里走些,喧闹声如潮水般退去,被身后密密麻麻,由远及近的脚步声淹没。
身后的人大声喊道:“林何!”
林枝意脚下一顿,不由得攥紧手中木箱的皮带,心中腹诽,她可真是时运不济。
她缓缓呼出一口气,慢慢转过身去,瞧见几个穿着粗布麻衣,家丁模样的人,手持棍棒,一看就不像良善之辈。
其中一人手臂上还有道触目惊心的伤痕,他站在几人中间,瞧这架势,应当是这帮人的头儿。
林枝意心中狐疑,这几人只知她叫林何并不知她真名,这般气势汹汹地找她到底有何目的?往日里她一向宽以待人,也未曾与谁结怨。
林枝意脸上堆起一抹笑容,那笑意浮于嘴角却不达眼底,说道:“各位兄台,找林某有何贵干呀!今日天色已晚,要不明日再说。”
她今日刚好带了蛇缠藤,若是他们非要纠缠,她就拿他们试试药性,看看真如医书上说的那般能让七尺大汉瞬间昏迷半个时辰吗?
那家丁头子依旧横眉冷蹙,语气恶劣地喝道:“我家老爷有请,劝您还是乖乖听话,我们这些粗人下手可没轻没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