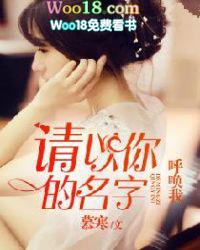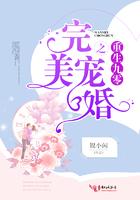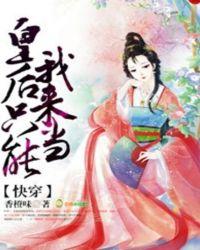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魏晋不服周 > 第205章 大魏的最后一天上(第2页)
第205章 大魏的最后一天上(第2页)
“他们不是死于无知,”阿禾声音清越,穿透夜风,“而是死于有人害怕知识。”她将陶瓮置于薪火台中央,点燃一圈油灯。“今天,我们不烧纸钱,我们点灯。每一盏灯,代表一条活在人心中的法律。”
灯火渐次亮起,映照出千张面孔。孩子们手持竹片,在地上默写《人身保护令》;老人们低声背诵《赋税透明法》;一对年轻夫妇抱着婴儿,轻声念道:“此子无论男女,皆有权入学识字。”
张守文默默取出那块“追问”青铜片,投入火中。铜片熔而不毁,最终化作一枚小小的印章,印文仍是二字:追问。
数日后,阿禾收到一封匿名信,无署名,仅附一首古诗抄录: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她认得笔迹??是当年国子监那位青年书生,如今的律察司使臣。她笑了笑,将诗贴于公示墙最顶端,下方加注一行小字:“正气不在天上,而在每一个敢问‘为什么’的喉咙里。”
秋去冬来,大雪封山。火种队的脚步却未曾停歇。一支由牧民组成的“雪路讲团”自发成立,背着简装《律镜简册》穿越祁连山脉,在每一座帐篷里宣讲《游牧行rights》;南方传来消息,长江沿岸已有十七个村落仿效“问答桩”制度,设立“水边问政石”;就连岭南蛮族也遣使求取《自治约法》,愿以铜鼓为誓,共建边地共治联盟。
腊月廿三,小年。阿禾正在整理年度《民问录》总卷,忽闻门外喧哗。启明飞奔进来,脸上带着罕见的激动:“阿妈!长安来了使者,带着天子亲诏!”
诏书内容简短却震撼:
“尔等播法于野,启愚为明,功在社稷。特赐‘律光’匾额一方,悬于敦煌微学堂。另准尔每年冬至入京,于太学开坛讲律,谓之‘岁问’,百官列席,听民声,察政失。”
使者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块由宫廷匠人打造的青铜板,正面镌刻《教育权》全文,背面则是一行小字:“此法天下通行,如有违者,人人得执此板以问之。”
阿禾抚摸着冰凉的铜面,久久无言。她忽然想起那个炭笔画画的女人,想起老农攥着半块腰牌昏倒在井边,想起乌仁娜在风中诵读“士兵非牲畜”时老兵们颤抖的肩膀……这一切,竟真的走到了今天。
除夕之夜,微学堂举行“守律宴”。众人围炉而坐,轮流背诵自己最爱的律条。轮到启明时,她站起来,声音清亮:“我想说的不是律文,而是一个问题。八岁那年我问阿妈:‘如果所有人都闭嘴,世界会不会黑掉?’今天,我可以回答自己了??不会。因为三年前,我在莎车城遇见一个哑巴女孩,她不会说话,但她用沙子写了整整一夜的《婚姻自由法》。第二天,全村女人跟着她学写字。所以,只要还有一个人能写下‘不’字,黑暗就永远赢不了。”
众人静默片刻,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阿禾含笑饮尽一碗酪浆,望向窗外。雪仍在下,覆盖了黄沙,也覆盖了旧年的血与火。但她知道,有些东西是雪压不住的??比如春天,比如人心,比如那些在寒夜里依然坚持发问的声音。
正月初七,立春。第一缕东风吹过玉门关。阿禾率队再度启程,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更西的疏勒与龟兹。临行前,她在薪火台留下最后一道命令:
“从今往后,《民问录》不再由我们编,而由各地微学堂自行汇编,每年冬至交汇于敦煌。我们要让这部书,真正成为千万人共同书写的历史。”
驼铃声远,黄沙漫卷。朝阳升起时,一只陶瓮被埋入新栽的杨柳树下,瓮中装着过去一年所有的提问与回答,还有一枚小小的青铜印章??“追问”。
百年后,后人掘地得瓮,开之,见文字如生,遂叹曰:
“此非藏书,乃藏魂也。”
而那枚印章,被收入太学博物馆,展签上写着:
“魏晋不服周??不服者,非不服天命,乃不服不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