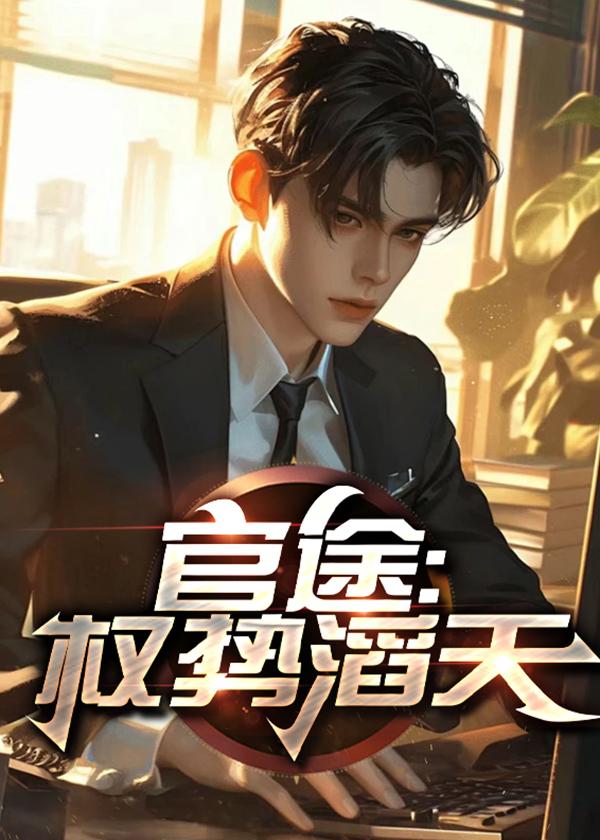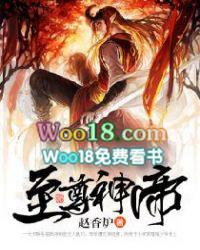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大早就来(第1页)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大早就来(第1页)
李可向来喜欢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
不过……
这也恰恰是朱元璋喜欢李可的原因。
因为李可总能给他提供完全不一样的思路,而走正道,他随便找个人,都能给他说出个一二三四。
在大善殿。。。
夜阑人静,李可卧于病榻之上,窗外寒风穿庭,吹得檐下铜铃叮咚作响。他双目微闭,额上尚有虚汗涔涔,梦中似见无数百姓跪伏道旁,口称“青天”,又忽转为火光冲天、尸横遍野,士绅举刀怒斥:“乱法之徒,人人得而诛之!”惊起时,冷汗浸透里衣。
婢女轻步进房,端来一碗温药。李可勉强坐起,接过碗盏,苦涩入喉,却觉五脏六腑皆被熨帖。他望了一眼床头那本翻旧的《官为何物》,书页边角已卷,墨迹亦有些晕染,却是他亲手所著,字字如钉,句句带血。
次日清晨,陈文远悄然来访。见李可气色稍复,方敢落座。二人对视良久,终是李可先开口:“杭州那边,可还安稳?”
陈文远低声道:“汪氏田产已抄没三分之一,族中两名京官遭贬外放,礼部尚书闭门谢客三日。民间传言四起,有说‘新政杀人不见血’,也有赞‘天子英断,奸邪伏诛’。但……”他顿了顿,“户部侍郎昨日在朝会上奏,请缓行审计之法,言‘察吏过严,恐伤士心’。”
李可冷笑一声:“士心?他们何时关心过民心?元末饥荒,饿殍塞路,这些‘士’躲在庄园饮酒赋诗;如今新政稍动其利,便哭天抢地,说是‘伤士心’?可笑!”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急报声??锦衣卫千户陆昭求见。
陆昭步入堂中,甲胄未解,神色凝重。他拱手禀道:“大人,襄阳密探来信:南昌按察使并未真正交账,其私设‘影库’七处,藏银逾万两,且与江西布政司通同舞弊,以‘灾损’之名虚报田亩,实则将税粮转售豪商牟利。更甚者,有人查出,该按察使三年前曾收受宁王旧部贿赂,包庇谋逆案证供灭迹。”
李可猛地撑起身子,眼中寒光迸射:“宁王余党?此事可上报陛下?”
“尚未。”陆昭摇头,“因牵涉宗室,锦衣卫内部已有异议,恐引风波。卑职以为,若贸然揭发,恐激起地方军政一体反扑,尤其他们已知朝廷派员巡查,正密令各地伪造文书应对。”
室内一时寂静如死水。
陈文远沉吟片刻,道:“此非一省之弊,乃体制之疾。高薪养廉虽立,审计虽行,然地方官场盘根错节,上下勾连,一人落马,百人遮掩。今若只惩个案,无异扬汤止沸。”
李可缓缓点头,目光渐深:“你说得对。我们打掉的是蛇头,可整条毒蛇仍在蠕动。”
他起身披衣,踉跄几步至案前,提笔疾书,不片刻写下三策:
其一,设立“巡按御史团”,由皇帝亲授印信,不受地方节制,每半年轮换辖区,专司暗访稽查,直通圣听;
其二,推行“政务公开榜”,凡州县钱谷出入、刑狱判决、徭役摊派,须每月张贴于城门口,百姓可对照举报;
其三,启用“连坐追责制”??凡属官贪腐,主官即便不知情,亦须承担失察之罪,降级罚俸,三次即罢免。
陈文远看罢,脸色发白:“这第三条……怕是要掀翻半壁江山。”
“那就掀。”李可声音平静,“若连责任都不敢担,还配做父母官?一个县令治下出大案,他自己却说‘不知情’,百姓岂能信服?官官相护,最伤人心。从今往后,谁坐在那个位子上,就得负那份责。”
三日后,朱元璋召集群臣议事。
当李可所呈三策宣读完毕,满殿哗然。
刑部尚书当场跪奏:“连坐之法,古所未有!况官员日理万机,岂能事事亲察?若因此获罪,谁敢任事?”
兵部侍郎亦附和:“巡按御史权力过大,形同监军,恐致地方掣肘,政令难行。”
唯有大理寺卿徐阶出列支持:“臣以为此策可行。唐有巡察使,汉有刺史,皆中央控驭地方之要举。今日之患,不在权太重,而在责太轻。官无惧畏,故敢妄为。若明定问责,则人人自警,弊自消矣。”
朱元璋默然良久,忽问:“李卿如今可在宫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