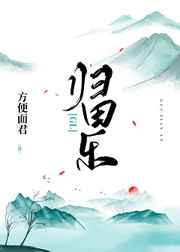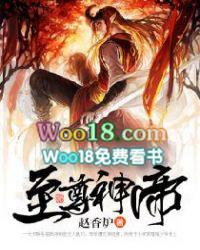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俗仙 > 305遇南而开遇马得主(第3页)
305遇南而开遇马得主(第3页)
“谢谢你们。”他说,“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礼物。”
然后他转身走去,背影渐渐融入晨光。
没有人看到,当他跨过山脊那一刻,脚下的草鞋悄然化作尘埃,随风飘散。但他留下的足迹,却深深烙印在泥土之中,多年不灭。
数月后,朝廷派出使者调查“逆俗思潮”,欲查封启蒙堂。可当官员踏入教室,看见墙上那一排排稚嫩却真诚的愿望时,竟伫立良久,最终下令:“此地不归官管,任其自立。”
他还悄悄留下一本《幼学琼林》,扉页题字:
**“或许,真正的教化,从来不在庙堂之上。”**
多年以后,那位小女孩果然建起了一座名为“守愿岛”的聚居地。岛上无高墙,无户籍,只有环形学堂与中央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每年清明,人们都会聚集于此,朗读三百个名字,唱一首没有曲调的歌:
>“我们在唱歌……
>别为我们哭……
>告诉未来的人,我们学会了笑。”
而林小凡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典籍中。
但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总有一个麻衣男子,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出现,为迷路的旅人指路,为病重的老妪煎药,为哭泣的孤儿哼一支不成调的童谣。
有人说他是神仙,有人说他是疯子,更多人说??
“他就是我们想成为却不敢成为的样子。”
某年冬夜,大雪封山,一间偏僻山村的祠堂里,几位老人围炉取暖,讲起了旧事。
“你们知道吗?”一位瞎眼老翁忽然开口,“二十年前,我差点饿死在雪地里。是一个不说话的男人救了我。他把我背回家,煮了一碗姜汤,临走时只说了一句:‘活着,比什么都强。’”
“我也听过!”另一人激动道,“十五年前瘟疫爆发,是我家门口出现一碗药,下面压着张纸条:‘喝完睡觉,明日好转。’”
“还有我!”年轻些的汉子插嘴,“去年我被打断腿,躺在破庙里等死。半夜来了个人,替我接骨,敷药,天亮就走了。我没看清脸,但记得他右手小指缺了一截。”
众人沉默片刻。
最后,老翁轻声道:“也许……他不是一个人。也许,他是所有愿意多走一步路的人,合在一起的灵魂。”
炉火噼啪作响,映照着每个人的面孔。
窗外,雪仍在下。
而在千里之外的西荒沙漠,那座灰白石碑上的文字悄然变化:
>**“所谓正常,不过是多数人的暴政。**
>**而真正的修行,是从敢于承认‘我不够好’,**
>**却又不肯因此低头开始。**
>**??后来者共勉。”**
风沙拂过碑面,带走一粒沙,又带来一粒新沙。
就像这个世界,永远在毁灭与重生之间徘徊。
但只要还有人愿意点亮灯火,
只要还有人心中藏着一句“我要”,
那么,
俗仙,就永远不会真正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