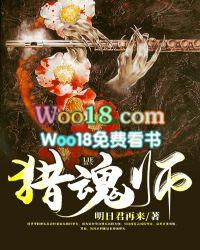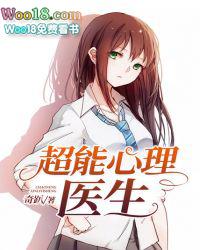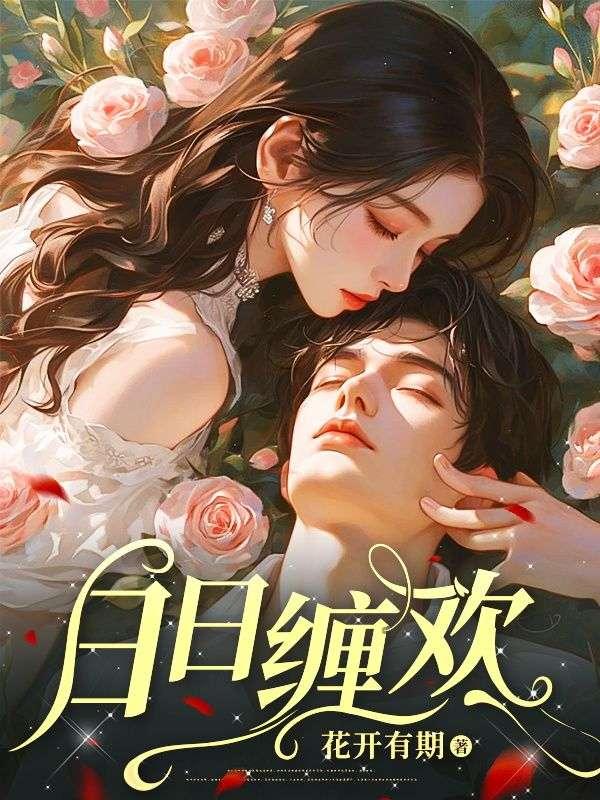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俗仙 > 310没法善良就凶到底(第2页)
310没法善良就凶到底(第2页)
黎明时分,雨停了。她已能用自己的手指在沙地上写下“光明”二字,歪斜却坚定。林小凡看着,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本是来点燃火种的,可这一次,却是他自己被照亮了。
临行前,她拉住他的衣袖:“你会回来吗?”
他摇头:“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但只要你继续写下去,我就一直在听。”
她点头,松开手。他走出庙门,回望一眼,只见她已坐在门槛上,捧着那本发光的册子,唇齿轻启,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声音不大,却穿透晨雾,惊飞林鸟。
他继续南行。越往边境,战火痕迹越深。村庄焚毁,尸骨半埋于荒草之间;幸存者蜷缩在岩洞中,靠野菜与树皮维生。然而就在一处废墟角落,他发现了一堵残墙,墙上用炭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是一首诗,题为《读书人不死》:
>“头颅可断墨不干,
>笔锋未冷骨犹坚。
>若问此身何所惧?
>不识一字是江山!”
落款只有一个字:“禾”。
林小凡呼吸一滞。阿禾!那个抱着焦边残纸逃命的少年,竟一路流亡至此,仍在坚持书写?他顺着诗句方向追寻,在一座塌陷的地窖中找到了他。阿禾瘦得脱形,左臂缠着发黑的布条,显然受过重伤,怀里仍紧紧抱着那支铅笔,身旁散落着数十张写满字的破布与碎陶片。
“你还活着?”林小凡扶起他。
阿禾睁开眼,瞳孔浑浊,却在看清来人面容的一瞬迸发出光芒:“是你……你说要去下一个能写字的地方……我跟着来了……可这里没人教我……我就自己写……写了好多……不知道对不对……”
他语无伦次,却拼命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模仿《论语》写的句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今我不识师,自学亦乐也。”
林小凡眼眶发热。这哪里是错字连篇的习作?这是一个灵魂在绝境中为自己点亮的灯!
他当场坐下,一页页为他批改,纠正音律,讲解典故。阿禾听得如痴如醉,仿佛饿极之人吞食珍馐。说到动情处,两人相拥而泣。
三天后,阿禾体力稍复,执意要随他同行。“我要把写下的东西带给更多人看。”他说,“哪怕只能换一顿饭,我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忘记怎么说话。”
林小凡答应了。他们一路南下,途中收容流浪儿童七人,皆愿习字。他们在一处废弃驿站建起临时学堂,用烧焦的木棍当笔,地面为纸,每日授课两时辰。消息传开,周边难民陆续前来,有人带来残破竹简,有人献出祖传字帖,甚至有一位老兵,跪着请他们教自己孙子认爹娘的名字。
第一百零一所启蒙堂,就这样在废墟中诞生。
某夜,林小凡独自守灯整理教材,忽听门外脚步轻响。抬头一看,竟是余沉舟站在檐下,蓑衣滴水,面容苍老许多,右腿微跛,显然历经磨难。
“你来了。”林小凡并不惊讶。
“我找了你三年。”余沉舟走进来,从怀中取出一只密封陶匣,“这是最后一支‘启明芯’??用东海鲛人泪、百年紫檀心和三百名自愿捐髓的学子骨粉炼成。它能让一本书自动复制内容,只要放在旁边,三日便可生成百卷。”
林小凡接过,沉甸甸的,仿佛托着无数人的希望。
“代价是什么?”他问。
“使用一次,施术者将失去声音。”余沉舟平静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林小凡摇头:“不必。我们可以慢慢抄。”
“可时间不多了。”余沉舟低声道,“衡律司残部正在集结,他们联合了几位守旧派大学士,准备发动‘净典之役’,要焚尽所有非官修书籍,重启‘禁智令’。朝廷内部已有动摇之声,若不能在三个月内让十万百姓识字并公开诵读新政,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林小凡沉默。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必须在这片焦土上,迅速建立起一百所以上合规学堂,并完成首批学生认证。
“那就加快速度。”他说,“我去西南最偏远的三十六寨,那里至今不通汉语,若能让苗、侗、瑶三族共学同文,便是最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