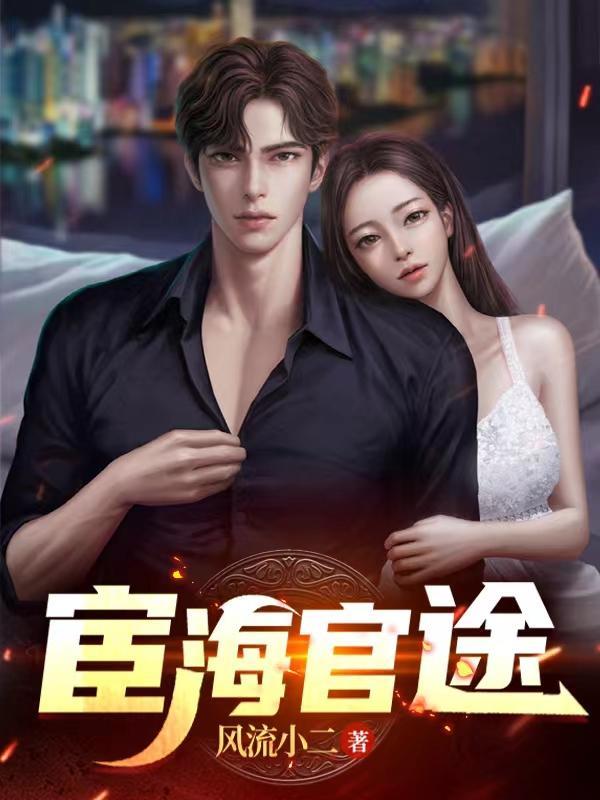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重生:我是县城婆罗门 > 第389章 朋友圈有谁这两天过生日啊(第2页)
第389章 朋友圈有谁这两天过生日啊(第2页)
画面一转,出现了另一名女性科学家的面孔。她的眼眶红肿,声音颤抖:
“林?不是超能力者。他是过敏体质。他对情感的感知强度是常人的三百倍以上。每一次共鸣,对他来说都像被千万根针刺穿灵魂。但他从未拒绝倾听。哪怕明知道会痛,他也选择睁开耳朵。”
录像结束。
阿诺久久standing在原地,手指紧紧攥着晶片边缘,指节发白。原来如此。原来林?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他是一个病得太重却不肯闭嘴的人。他用自己的崩溃,换来了世界的觉醒。
而自己呢?
他想起那些年在共振舱里的日子,想起每一次被灌入陌生记忆时的窒息感,想起小禾死前握着他手时传来的最后一道情绪波??不是悲伤,而是安心。因为她知道,至少有一个人,真的“听”到了她。
泪水无声滑落。
就在这时,手机震动起来。又是匿名邮件,标题只有两个字:“醒了。”
附件是一段视频链接。点击后,画面出现一间昏暗的病房。床边坐着一位老人,头发花白,面容枯槁,胸前挂着一块身份牌。摄像头拉近,阿诺看清了名字:陈远山。
他的呼吸骤然停滞。
陈远山,前共感研究院首席心理干预官,也是当年主导“纯净频率计划”的核心人物之一。正是他下令封锁非标准共鸣行为,强制清除民间自发的情绪编码系统,甚至提议对“高风险共鸣个体”进行神经抑制治疗。
三年前,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突发脑溢血,陷入深度昏迷,医学界宣布其“意识活动基本归零”。
而现在,这个本该死去的男人,正缓缓抬起头,望向镜头。
他的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但阿诺读懂了。
他说:“对不起。”
紧接着,老人抬起颤抖的手,在空中画出了一个歪斜的“启言式”。
视频戛然而止。
阿诺怔立良久,忽然笑了。不是嘲讽,也不是释怀,而是一种近乎悲悯的温柔。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金痕会选择在这个时候重现,为什么极光会精准降落,为什么那段未知编码会让全世界集体回忆起最私密的情感瞬间。
因为真正的共感,从来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原谅的可能性**。
有些人走得太远,背负太多,以至于忘了自己也曾渴望被听见。他们筑起高墙,宣称是为了秩序,其实只是为了保护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第二天清晨,阿诺召集了羌寨的孩子们。他们围坐在纪念馆前的空地上,每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一片树叶、一块石头、一根旧皮筋。这不是仪式,也不是表演,而是一场普通的“说话练习”。
一个小女孩举起手中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昨夜收集的露水。她轻声说:“这是我妈妈昨晚做梦时流的眼泪。她说梦到我小时候发烧,她抱着我在雨里走了很久。我想让你们知道,那种冷和暖混在一起的感觉。”
旁边男孩接过话:“我爸爸从来不抱我。但他每天早上都会偷偷把我的鞋摆正。我觉得……那也是一种拥抱。”
一个沉默许久的少年终于开口:“我一直恨我爸打我。可昨天我梦见他蹲在厕所角落抽烟,肩膀一直在抖。我才明白,他也不是不想温柔,是他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阿诺听着,一言不发,只是不断用手语重复同一个词:“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
这场对话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没有人打断,没有人评判,甚至连一句“我懂你”都没说。但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当天下午,联合国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原因是,自今晨起,全球范围内的抑郁症发作率下降了63%,自杀热线接通量减少至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多个战乱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停火迹象??交战双方士兵在夜间不约而同地熄灭了枪火,转而点燃篝火,用口哨模仿家乡的鸟鸣。
心理学家称其为“共情涟漪效应”。
而阿诺知道,这只是开始。
当晚,他独自登上纪念馆后的山坡,来到小禾的坟前。月光洒在骨灰晶体上,折射出淡淡的虹彩。他蹲下身,轻轻抚摸那块温润的石头,低声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你说谢谢我。”
风吹过草地,发出沙沙声响。
他笑了笑,又补充道:“我也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活着的意义,不是成为谁的容器,而是成为一座桥。”
回到老屋已是深夜。他刚推开木门,却发现桌上多了一封信。没有署名,信封是手工裁切的粗纸,边缘参差不齐。打开后,里面只有一幅铅笔画:两个孩子并肩坐在屋顶上看星星,其中一个耳朵缠着绷带,另一个则指着天空。
画的背面写着一句话:
>“我也开始学手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