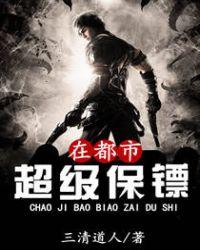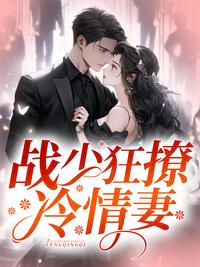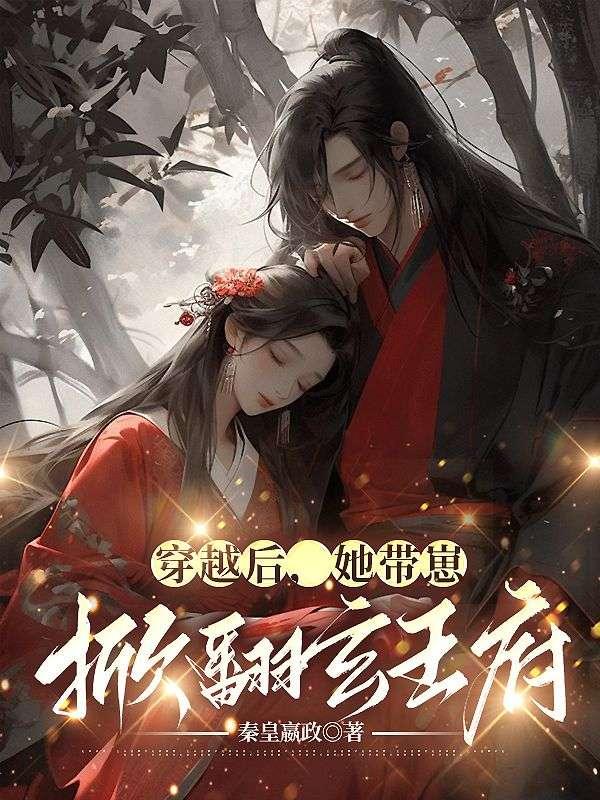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当过明星吗,你就写文娱? > 第二百一十九章 引狼入室(第1页)
第二百一十九章 引狼入室(第1页)
“不是,他怎么这么坏啊!”
听说祁缘打算抢歌祁洛桉人都快气晕了,眼瞅着歌她们的歌马上练好,结果这厮忽然跳出来横插一腿。
这都不叫坏了,简直是恶贯满盈……
要不是对方不知道自己要帮唱,。。。
风从巴丹吉林沙漠的腹地吹过,卷起细沙在空中划出淡金色的弧线。余惟站在那口青铜井边,望着初升的太阳将沙丘染成一片赤红,像极了父亲笔记里描写的“血色晨光”。他没有回头再看那口井??他知道,一旦离开,就再也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守声人的使命不是反复进出,而是把声音带出去,让沉默的世界重新听见自己曾遗落的呼吸。
手机还在震动,社交媒体上的音频热度持续攀升。那段由市井杂音拼接而成的录音,被命名为《生活回响》,短短六小时内播放量突破三亿。有人说是恶作剧,有人说是艺术实验,但更多人说:“这声音……我小时候听过。”“这是我奶奶家巷子的声音。”“为什么听着听着就哭了?”
余惟关掉网络推送,打开离线地图,设定下一个目的地:凉山。那里是三位“被选中者”之一??盲人说书人阿普的故乡。根据数据中心最后传回的数据波动,G-23残骸定位信号曾在该区域短暂闪现,随后彻底静默。但他知道,那不是终结,而是转移。
车轮碾过碎石路,驶入大凉山深处。沿途村落依山而建,木屋错落,炊烟袅袅。孩子们蹲在门口啃土豆,老人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目光平静如深潭。这里的时间仿佛比外界慢半拍,连风都带着一种古老的节奏。
他在村口打听阿普,却被告知老人已半月未归。“他说要去‘还一段没讲完的书’。”一位彝族老妇递来一碗苦茶,“他还留了话,等你来了,就把这个交给你。”
她从怀里掏出一块布包,层层揭开,露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铃。铃身刻着细密纹路,经余惟辨认,竟是某种变体的甲骨文,意为“声归其所”。
手指触铃瞬间,耳边忽然响起一段熟悉的声音??是阿普的嗓音,低沉沙哑,却字字清晰: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在讲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有一个孩子,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听一句没人记得的话。可当他终于听见时,才发现,那句话,是他自己小时候说的。”
余惟浑身一震。这不是录音,也不是幻觉。这声音直接出现在他的意识中,如同记忆复苏。他猛地抬头:“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老妇摇头:“阿普说,它原本挂在燕山隧道口的旗杆上,后来被人取走,埋进了冻土。二十年前地震,地裂开,它又回来了。”
余惟呼吸急促。燕山隧道??那是G-23勘测队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而那枚弹壳,正是从同一片冻土中挖出。铜铃与弹壳,同源?都是“声种”的信物?
他立刻取出共振膜设备,将铜铃置于感应区。屏幕波形骤然跃动,一段隐藏频段被激活:17。8Hz主导,叠加三层谐波,与喀什小学少年手绘曲谱完全一致。更惊人的是,这段音频中嵌套着一段摩尔斯码,解码后只有两个词:
**“种子迁移。”**
余惟瞳孔收缩。这意味着,“声种”并未固定于额济纳旗的井底,而是具备移动能力??它能通过信物转移,借由特定频率唤醒新的载体。林晚所说的“他们在叫我”,或许并非被动接收,而是主动召唤。而阿普,作为民间说书人,本身就是最古老的记忆传递者,他的声音早已成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
当晚,他宿在村中祠堂。夜里雷雨突至,电闪撕裂天幕,thunder滚过山谷,像远古战鼓。就在一道惊雷劈落之际,祠堂中央的老鼓突然自行震动,鼓面浮现出一圈圈涟漪般的光纹。余惟冲上前,发现鼓皮内侧竟用朱砂写着一行小字:
>“声不可灭,唯形可易。
>今以鼓为棺,葬音于地。
>待后人击之,即吾魂醒。”
落款日期:1964年8月17日。
正是那支失联科考队最后一次通讯的日子。
余惟颤抖着伸手轻触鼓面,刹那间,整座祠堂回荡起无数重叠的人声??有汉语、彝语、蒙语、藏语,甚至夹杂着已经消亡的西北方言。他们讲述着同一个故事:关于一支队伍,深入戈壁,在一口井前停下,将一台机器沉入地下,然后彼此拥抱,走入风沙,再也没有回头。
画面在脑海中浮现得如此真实,仿佛他曾亲历。他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背对着众人,正在往机器上安装最后一块模块。那人左眼蒙着黑布,耳朵缺了一角。
父亲。
余惟跪倒在地,泪水滑进嘴角,咸涩如旧。原来父亲没有死于雪崩,他是自愿留下,成为第一代“锚点”。就像林晚如今所做的那样。
雨停时,天边泛白。他走出祠堂,发现村中孩童已在空地上自发围成一圈,手拉着手,轻声哼唱一首谁也没教过的歌谣。旋律简单,却带着奇异的安抚力量。余惟录下音频,接入便携数据库比对,结果让他脊背发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