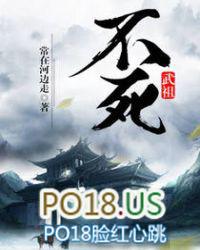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BLOOD(强制H) > 超短脑洞 一剑(第1页)
超短脑洞 一剑(第1页)
一花,一舞,一剑,一江湖
—
鎏金烛架上的烛泪盘踞成一摊凝固的死水,在浑浊固体中挣动的淡光似是要将那闪烁着的烛盏浸染地更加炽烈。
轻柔飘渺的丝竹管弦奏起,继而是琵琶清脆婉转的曲调,在帝王手中晃动的金樽内壁流连不去。
布菜的宫女如飞鸟般轻盈,垫着脚尖有序离去,唯余一室王侯将相高谈阔论。
他居于高坐,啜饮盏中的琼浆玉露,目光凝在衣裙娉婷的舞姬之上。
没有同舞相伴,只她一人。
伴乐有一瞬间地静止,舞未启,乐未奏。
身姿柔软的舞姬便犹抱琵琶半遮面,微微低着头,云鬓间的白玉步摇便跟着她的动作一摇一摆。
如雾般朦胧的丝带遮住舞姬的双眸,宽大的水袖间,他明明看不清她的容貌,偏觉得她的眸里装了一汪秋水。
似是终于反应过来,奏乐忽地奏起。
他便见那舞姬轻点赤裸的双足,挥荡的水袖散了满室的暗香,在逐渐迷蒙的视线中,似是要突破阶层的天堑,拂过龙袍上的暗纹。
“…”帝王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目光死死盯着她柔韧的腰腹。
他看透舞姬看似娇柔实则暗含杀机的身躯,也对即将开场的闹剧了然于心。
散落的青丝间,他看到舞姬微勾的唇角。
交谈声早已戛然而止。
鼓点声与乐琴声愈发急促,如倾颓的雨幕,牵引着舞姬旋转的脚步,亦是催促血腥的开幕。
一达官显贵看得痴了,再次回过神时,不知何时对上了舞姬那被蒙住的双眼。
喉间被心跳闷地酸胀,他还没来得及喝彩些什么。
忽见舞姬舒展的双臂间,有一柄迸发着寒光的短匕刺破水袖,带着狠辣的力度直直穿透他的咽喉。
“咯…咯…”惊叫被刀刃捅穿,撕裂的声道已无法支撑他大呼小叫,能呈现于世人的唯有黏腻血液喷涌的声音,和暴突的双眼。
他垂下断裂的头骨,生生被刀刃钉在坐席之上。
舞仍起,曲仍奏。
舞姬轻快的双足沾染上飙射的血液,却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人群鱼贯而出。
唯有她一人立于高堂,旋转开的裙摆冷若冰霜,在杀戮之中与血腥作伴。
最后终在帝王滚烫的视线中谢幕。
数日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