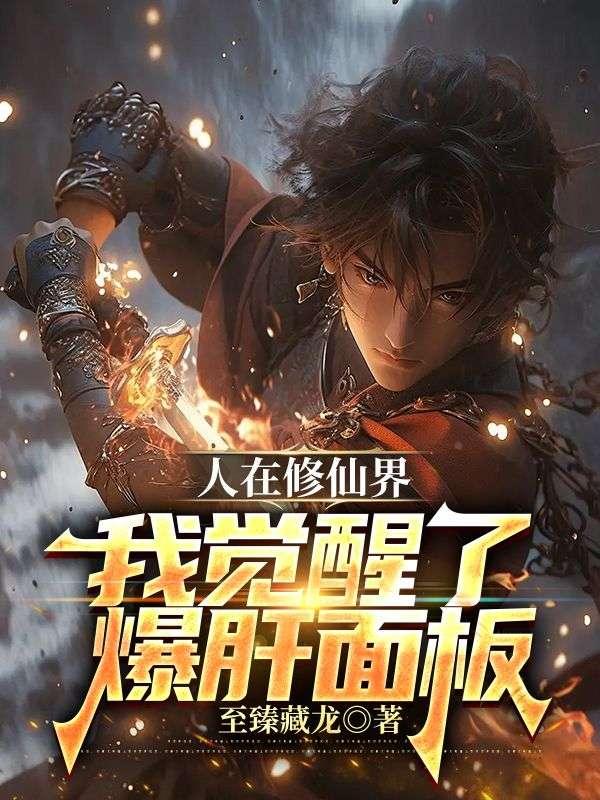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剑三】盛唐 > 第十七章(第1页)
第十七章(第1页)
【八方游】载着李思怡一行四人离开了逻些城,在李裳秋的强烈要求下,李思怡放弃了自己衣柜里花里胡哨的外观,老老实实的穿着深色的藏袍,成天成天的跟啾啾和小酒缩在车厢里。
马车一路向东。车轮碾过了逐渐返青的草甸。越往东行,地势起伏愈发剧烈,空气也似乎变得更加稀薄而凛冽。
旅途中,他们时常能遇见虔诚的吐蕃人,或独行,或结伴,沿着蜿蜒的山路,一步一叩首,进行着艰苦而漫长的转山朝圣。他们古铜色的脸上刻满风霜,眼神却纯粹而坚定,口中低声诵念着经文,那强大的信仰之力,仿佛能与这亘古的雪山共鸣。李思怡趴在车窗边,安静地看着这些身影,心中对这片土地和在这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了更直观也更复杂的感受。
如此前行了十天,她们来到了夏贡拉山口。山下的植物已经绿了一片,上到山口却寒风如刀,裹挟着雪粒,吹得车帘猎猎作响。
李裳秋给三个小姑娘裹上了厚厚的毛毯,哪怕直到【八方游】根本不需要车夫,自己就能前行。但这里山路崎岖,坡度陡峭,她还是不放心的亲自坐到车前看着马匹在山壁上前行。
虽然呼吸比平日费力,胸口也有些发闷,但是她们终究还是安全的翻过了夏贡拉山口,往下走到一处相对平缓的背风坡时,眼尖的啾啾忽然指着前方不远处:“钦波,您看!那里好像有人!”
离开红山宫来到小院的啾啾和小酒被众人千叮咛万嘱咐不可再叫李思怡郡主,小酒不接受用别的称谓称呼李思怡,最后是啾啾带着小酒直接称呼李思怡“钦波”(藏语:主人)。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前方的路边有个半跪着的青年女子,约莫二十上下,穿一身紫黑配色的劲装。再走近一点,才看见她身前还躺着一个跟她同样衣着的女子,面色青紫,双目紧闭,显然是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已陷入昏迷。
李裳秋勒住马车,眉头微蹙,目光锐利地扫视四周,确认并无埋伏或其他危险。她常年行走江湖,深知高原反应的凶险,尤其是对初入此地、身体不适者,几乎是致命的。
“是万花谷的弟子。”李裳秋低语,目光扫过女子衣领上刺绣的银色纹样。七秀坊与万花谷、长歌门并称大唐三大风雅之地,门下弟子也时常往来交流,素有交情。
半跪着正在给她做检查的万花弟子也发现了他们,她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却写满焦急与疲惫的脸庞,眼中带着恳求,声音因急切而有些嘶哑:“前方可是路过的朋友?在下万花谷弟子言绻,我师妹言荃突发恶疾,危在旦夕,恳请援手!”
李裳秋沉吟片刻,她对万花谷印象不坏,又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她低头看向钻出车厢的李思怡,用眼神征询她的意见。毕竟,这马车是李思怡的“坐骑”,此行她虽是护送者,却也尊重小外甥女的想法。
李思怡看着言绻那几乎要哭出来的眼神,又看看危在旦夕的言荃,见死不救实在有违本心。她用力点了点头,小脸上是超越年龄的认真:“姨妈,我们要是不帮忙,这个姐姐会死的!我们一定要帮忙!”
李裳秋见她如此说,也不再犹豫,当即道:“好!快将人抱上车!”
言绻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的言荃抱上了【八方游】。本来车厢里只有李思怡、啾啾和小酒三个小孩子,空间还算宽敞,言绻和言荃一上车,特别是言荃还得平躺在车厢里,这下子车厢里就有点拥挤了。啾啾和小酒干脆退到了车厢外,跟李裳秋一起坐在驾车的位子上。
言绻也没有时间客气,指尖闪烁着淡绿色的柔和光芒,迅速在言荃头颈胸腹几处大穴拂过,正是万花谷绝学《太素九针》中的镇脉定魂手法,用以稳住她最后一线生机。
“多谢诸位援手!师妹她修为尚浅,不适应这极高之地,之前为了救治山下牧民又耗费了大量精力,这才……”言绻语带哽咽,满是自责。
“言荃姑娘不必多礼,救人要紧。”李裳秋沉稳道,一手一个护住啾啾与小酒避免她们落下车去。
为了缓解言绻的焦虑,也为了让李思怡多了解外界,李裳秋有意无意地引着言绻说话。言绻心怀感激,又见李思怡虽年幼却眼神灵动,充满好奇,便也陆陆续续地讲述起她们此次出谷历练的见闻。
她讲起在陇右道,为饱受风沙之苦、患有严重肺疾的牧民老者施针缓解咳喘;讲起在剑南道偏僻村落,遇到因山洪家园被毁、缺医少药的村民,她们就地取材,配制草药救治伤患;还讲起在淮南道,目睹富庶城镇中,仍有贫苦人家因无钱请医,小病拖成重症的无奈……
言绻的声音温和,讲述的故事没有过多渲染,却格外真实。李思怡听得入了神。这些故事,与她前世在贫困山区见过的景象何其相似!她仿佛透过言绻的讲述,看到了大唐广袤疆域下,不同阶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有边塞牧民的坚韧与艰辛,有山村乡民的淳朴与无助,也有城镇贫民的挣扎与无奈。这远比在红山宫或李守礼小院里听到的更加鲜活,也更加沉重。
在【八方游】平稳快速的行驶下,他们终于在天黑前抵达了在舆图上计划晚上休整的金岭乡。他们终于在天黑前抵达了计划中晚上休整的金岭乡。这是一处坐落在河谷地带的小小村落,海拔已降低许多,空气也湿润了些。李裳秋帮着言绻将依旧昏迷但面色好转的言荃抬进了提前联系好的一户干净民居。
李裳秋帮着言绻将言荃抬进了借宿的民居,言荃的脸色虽然依旧苍白,但青紫已退,呼吸也渐渐平稳绵长,算是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安顿好言荃,言绻再次郑重向李裳秋和李思怡道谢。月光透过简陋的窗棂洒入屋内,映照着言荃依旧苍白的脸,言绻心中的感激与后怕交织。她犹豫了片刻,目光落在旁边安静站着的李思怡身上,终是唤住了准备去安排食宿的李裳秋,语气带着谨慎与关切:
“李前辈,请留步。晚辈……还有一事冒昧。”她微微欠身,看向李思怡,“一路行来,晚辈观小妹妹面色,似有倦怠之色,不似寻常孩童红润,唇色亦略显淡白,缺乏血色。这高原路途艰辛,最是耗人气血。晚辈师承万花谷,略通岐黄之术,心下实在难安……可否让晚辈为小妹妹请个脉?若能无恙,大家也都安心。”
李裳秋停下脚步,转过身,目光如炬,仔细审视着言绻。见她眼神清澈坦荡,眉宇间只有纯粹的担忧,并无半分算计,又想到万花谷“活人不医”之名虽显孤高,但其医术确实冠绝天下,让她瞧瞧思怡的情况,或许能发现逻些城医者未曾察觉的隐忧。她略一沉吟,便点了点头:“言姑娘有心了。那便有劳。”随即对李思怡柔声道:“思怡,过来,让言姐姐帮你看看。”
李思怡乖巧地走到屋内那张略显粗糙的木桌旁坐下,伸出自己细小白皙的手腕,轻轻放在言绻临时取出垫在桌上的一个小巧布制药枕上。言绻收敛起所有杂念,屏息凝神,伸出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指腹轻柔却精准地搭在李思怡的腕间“寸关尺”三部。
几个呼吸后,她示意李思怡换另一只手。
言绻的眉头微不可察地蹙起,面色变得有些凝重,看向李裳秋,语气带着一丝沉重:“前辈,小妹妹的脉象……略显细弦,尤其左关弦象明显,按之略有滞涩之感,这是情志不舒,肝气郁结之兆。右关部脉象偏弱,濡软无力,是思虑过度,损伤脾气,运化乏力所致。心脉)亦略显浮数,乃是先前受过极大惊悸,心神未稳。”
她顿了顿,看着李思怡清澈的眼睛,心中叹息,继续道:“《内经》有云,‘悲则气消’,‘思则气结’。小妹妹年幼,脏腑娇嫩,这般忧思悲恐交织,最是耗伤心脾,暗损精血。若长此以往,非但影响生长发育,更恐……恐折损寿元根基。”
“什么?折损寿元?!”李裳秋尚未开口,一直紧张关注着的啾啾先失声叫了出来。她一贯沉稳细心,少有如此失态的时候,此刻脸色煞白,眼中瞬间盈满了惊恐与心疼。小酒的汉语学得还不太熟练,未能完全听懂,但见啾啾如此反应,也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个箭步冲进房间,紧紧站在李思怡身后,眼神警惕又带着敌意地看向言绻。
李裳秋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如同覆上了一层寒霜。在逻些城时,只当思怡是悲伤过度,慢慢将养就好,城内汉医医术有限,竟未诊出如此深层的隐患!她心中又是懊恼又是后怕。
言绻见她们神色,连忙宽慰道:“万幸,万幸小妹妹年纪尚小,生机蓬勃,如初升之阳,恢复力强。如今及时察觉,悉心调养,为时未晚。只是日后,定要极其讲究养生之法,此非依赖药石所能速效,重在‘调摄’二字,需持之以恒。”
她细细道来:“其一,调畅情志最为关键。需尽量让她心境开阔,避免再度受到大的刺激与悲伤。可引导她多接触自然生机勃勃之物,或习练一些舒缓心神的功法。其二,饮食需格外注意。宜温软易化,少食生冷油腻。可常用些健脾养心的药膳,如莲子、百合、山药、红枣熬粥,或是用合欢花、玫瑰花泡水代茶饮,疏肝解郁。其三,起居有常,保证充足眠息,不可过度劳神。其四……”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道,“若有得闲,能往万花谷一趟,让孙爷爷看看,更为保险。”
“孙爷爷?”李裳秋敛目,“可是医圣孙思邈老先生?”
言绻有些不好意思地点头,颊上飞起一抹红晕:“正是家师祖。我今年才初次与师妹出谷历练,见识浅薄,怕诊断拿捏得不十分稳妥。若能得孙师祖亲自诊视,开方调理,自然是最令人放心的。”她顿了顿,声音更低了些,带着难以启齿的恳求,“只是……不知几位目的何处,是否……与我们同路?师妹此番高反甚是凶险,唯恐伤及头颅根本,在这吐蕃地界,我实在……实在找不到其他可靠的帮手了。”她颊上飞红,“也不知几位目的何处,是否同路。”
她深知自己的要求近乎得寸进尺,对方已救了师妹性命,自己却还想蹭车一路同行。但为了师妹的安危和后续的彻底康复,她也只能厚着脸皮恳求,眼中满是忐忑与期待。
李裳秋看向李思怡,按计划她们需乘坐马车到达长安西北的广通渠渡口,乘船过通济渠南下扬州,大方向上倒也顺路。
李思怡更没有想别的,两个花姐就在眼前,所求也只是蹭个车,她还有机会能前往万花见识见识,甚至还有可能见到孙思邈!她还要什么自行车?果断点头同意,“顺路的!言姐姐,我们一起走吧!”
言绻见她们竟如此爽快应允,心中感激得无以复加,只觉恩情如山,一时不知如何表达,只能连连道谢,暗暗发誓待回到万花谷,定要倾尽所能报答这份救命与援手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