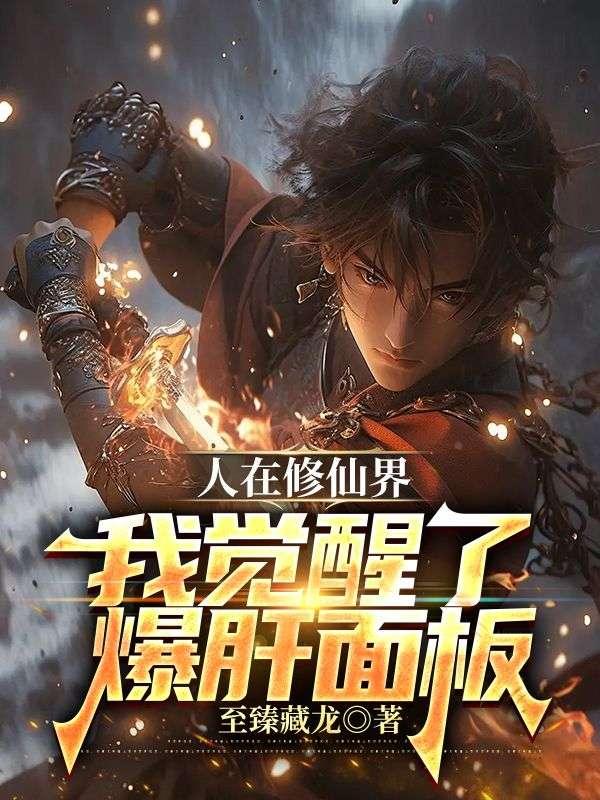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大清噬银黑洞的金钱美女局 > 第174章 王金华押赴伊犁(第1页)
第174章 王金华押赴伊犁(第1页)
杭州城北门的官道上,一早便停了辆囚车——车轮裹着厚棉垫,车栏没装尖刺,连押送的差役都没挎长刀,只别着根短棍,跟寻常流放的阵仗截然不同。王金华蹲在车边,正小心翼翼摸腰间的蓝布包,里面鼓得像塞了团棉花:三杆磨得笔锋发亮的狼毫(是狱卒从家里带来的旧笔,说“写字不硌手”)、一叠裁得方方正正的竹纸、小块磨得光滑的松烟墨,还有用油纸三层裹着的粗粮饼(儿子金少棠探监时塞的,他咬过两口就舍不得吃,说“路上当念想”),最底下还压着张皱巴巴的纸,画着歪歪扭扭的“钱庄贪腐流程图”,是他在天牢里偷偷画的。
“王大人,别磨蹭了,再不走赶不上正午的驿站!”差役老张递来个粗布水壶,壶口用热水烫过,还冒着热气,“您那布包别斜挎,揣怀里,过会儿起风,别吹跑了纸——昨儿个我特意跟驿站要了块油布,晚上能裹着纸笔防潮。”
王金华接过水壶,指尖蹭到壶身的温热,鼻子一酸,把布包往怀里紧了紧:“谢张大哥……这里面不光是纸笔,我还记了些真事,比如金满堂十年前怎么靠给柳仲文牵线洋行,每年分润3万两;吴世安去年怎么滥发200张空票,坑得西乡十户百姓卖地——这些都得写进书里,让后人知道钱庄的黑幕有多黑。”
老张蹲下来系鞋带,抬头扫了眼围观的人群——没见扔菜叶、骂脏话的,反而有几个穿短褂的粮农凑在前头,眼神里没敌意,便多嘴唠了句:“您这心思比陈维翰强百倍!那老小子上月斩头,临刑前还从怀里掏银票,说‘给刽子手两锭,让刀快些’,到死都想着贪!”
这话刚落,人群里突然挤过来个扛锄头的老农,皮肤黝黑,手上全是老茧,往王金华手里塞了个还热乎的玉米窝头,窝头缝里夹着几粒红豆:“王大人,俺是西乡李老三!您还记得不?去年俺家娃腿摔断了,想贷5两抓药,您手下的典吏说‘没地契?贷个屁!’,最后俺只能把耕牛卖了,娃差点截肢!现在您能揭贪腐,这窝头您拿着,路上饿了啃两口——是俺家娃特意给您留的,说‘能改的官就是好官’!”
王金华捏着热乎的窝头,指节都泛白,眼泪差点掉下来:“李老哥,以前是我瞎了眼,纵容手下坑百姓……这书我一定写细,把典吏怎么要好处、掌柜怎么改账本,全写出来,让以后没人再像您这样受委屈!”
李老三咧嘴笑,往人群里喊:“大伙儿让让!王大人要去写书赎罪,别挡道!”周围百姓立马往后退,还有人喊“王大人路上保重”“写好点,让当官的都看看”。
差役老张吆喝声“启程”,王金华没上车,跟在车边步行——他想最后看看杭州的变化。路过钱塘钱庄时,他猛地停住脚:门口的红漆柱子上贴满了告示,最显眼的是“粮农无息贷款”,李正清坐在木桌后,正给个穿补丁短褂的年轻汉子登记,汉子手里攥着张纸,笑着喊“俺贷30两修水渠,保长担保就行?不用押地契?”,李正清点头说“对!明年秋收还,一分利息不用给”。
“以前您当藩台时,钱庄放贷得押三分之一的家产,还得给‘跑腿费’,现在多好。”老张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语气里带着惋惜,“俺前儿个听驿站的人说,李掌柜推的无息贷款,救了江南五十多户粮农,有的还把以前借的高利贷还上了,再也不用躲债了。”
王金华没说话,从怀里掏出纸笔,借着囚车的木板蹲下来写——笔尖划过纸页沙沙响,他写:“昔年余任浙江藩台,收金满堂贿银五万两,默许其漕银暗抽;见吴世安滥发空票,百姓哭诉,却视而不见——今见李正清无息贷粮农,百姓欢颜,余愧甚!”
刚写两行,远处传来马蹄声,整饬署的文书骑着马奔过来,手里拎着个布包:“王大人!肃大人特意让我送来的!这里面是十刀麻纸、两块松烟墨,还有封给伊犁知府的信,让他给您找个带火炕的屋子,冬天能生炉子,别冻着手——肃大人说,您这书比啥都重要!”
王金华接过布包,手指抚过麻纸的纹路,眼泪终于掉下来:“替我谢肃大人……我就是个罪人,没想到他还这么看重我。”
文书笑着说:“肃大人说,能认错、能赎罪的,就还是有用的人!您写的稿子,将来能刊印出来,让全国的官都看看,贪腐到底害了多少百姓!”
夕阳西下时,队伍停在余杭驿站。老张端来碗糙米饭,上面卧了个金黄的荷包蛋——是老张自己省下来的:“您多吃点,写字费脑子。俺押送过不少贪官,有哭的、有闹的、有装傻的,像您这样抱着纸笔不撒手的,还是头一个。前儿个押送郑裕丰去黑龙江,那老小子还跟驿卒要酒喝,说‘老子以前天天喝好酒,凭啥现在喝糙茶’,您比他强太多了!”
王金华拿起筷子,却没动,反而掏出纸笔,借着油灯的光接着写:“余记金满堂曾言‘漕银抽成稳赚不赔’,今思之,其赚之银,皆百姓血汗也——有粮农因无银买种,卖儿鬻女;有商贩因空票兑银无门,上吊自尽……此皆余之过也!”
油灯的光晃得纸页发亮,王金华写得手指发酸,却舍不得停——他把写好的纸一张张叠整齐,用麻线捆成捆,塞进蓝布包最底下,又用油布裹了两层,生怕夜里下雨淋湿。老张看着他忙活,忍不住说:“您这么看重这书,将来肯定能写好。”
王金华抬头笑了笑,眼里有了以前没有的光:“这书不是给我自己写的,是给那些被钱庄坑过的百姓写的,是给以后当官的写的——我得写好,不然到了伊犁,都没脸面对那些被我害过的人。”
夜里,王金华躺在硬板床上,怀里紧紧抱着布包,像护着稀世珍宝。窗外的月光洒在官道上,虽远,却亮得晃眼——他知道,伊犁的路还长,但只要这纸笔还在,他的赎罪之路,就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