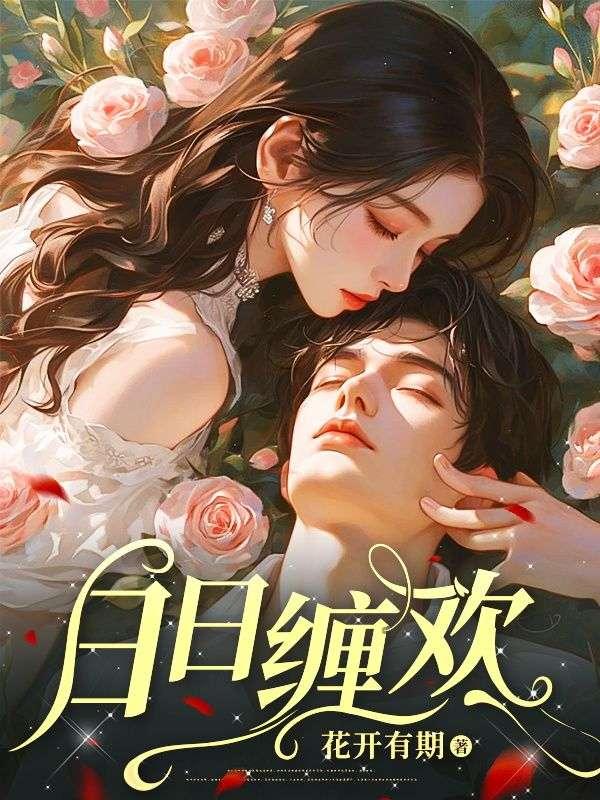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怀孕后下嫁给他 > 35再相见(第2页)
35再相见(第2页)
“那小子功夫了得,跟丢了很难再追上,咱们快马加鞭再去扬州,简直会乱上加乱,罢了罢了,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我们这些外人掺和也掺和不了,而且人多了闹大了几个孩子名声全毁了,元修你请几个人赶紧去保护你妹妹。再怎么样千万不要出人命。”
“好,我知道了。”
现在找几个可信的护卫很难,杭家以前没有给小姐准备什么护卫,因为她进出的都是宫廷侯门,窦玄又时常在她身侧,弄护卫实在有些多此一举。没办法,杭元修想要玉淑身边只有一个“霜兰”护着,便只能硬着头皮给自己的妹夫萧迹书信一封,看他能不能帮忙。
这个萧迹在他胞妹死后,就时常疯疯癫癫,时常夜宿花柳之地,而且他玩弄的那些女子,他见过一次,那些女子脸上总有一两处像他妹妹,实在让他感觉恶心至极,但是杭元修知道他能力出众,底下有一群影卫和其他组织,各个武功高强,还有很多奇人术士,和当今皇上关系匪浅,如今只能厚着脸皮去求他。
他在信里道明了前因后果,三天后便得到了飞鸽传书的回信,上面只有一个“好”。看到这封信,他心中石头总算落了地。如果玉淑要和窦玄回来,白家不肯和离放人,那些人有能力让玉淑回来。
此时,在一处山间的竹屋处,屋外梅香幽淡,一名半披半束发的青衣男子闭着眼眸正端坐在木椅上弹奏古琴,琴声幽而怨。屋内的焚香炉里飘出寥寥烟雾,是柔和甜的味道,只有千金的龙延香才有的味道。屋内放着带着樟木叶味的各种古籍整齐得堆在书架上,木几上放着一对青瓷瓶,上插着一支瘦梅。
听到琴声,几个人从密竹林之中朝着屋走去,很快琴声一停,众人一齐跪地。
萧迹吩咐完了这次任务,又道:“只需保护她的安全,其他无需插手。”
他们走后,萧迹来到屋内东侧靠窗处,桌案棋枰还有残局未能完成,萧迹先执黑子自言自语道:“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庄闲事…”
他又执白子道:“又是个无情无义的女子,跟你一样。”
”她长大了后,明明五官这么相似,但就不像你了。”
“果然你是独一无二的。”
“不知道她的孩子像不像你,我不能白帮忙,我想要个孩子。毕竟他们需要一个新主人。”
“如果不像你,我就不要了。”
“放心,你别担心我对你妹妹做什么,你们这样的女子我避之不及。”
他的头很痛,有时候这种诡异的行为反而能缓解他的头疼。
元宵一过,白青墨就又得忙了,白天他常常不在家。
每天走前吻吻枕边人的脸颊对他来说已经是习惯,这时候玉淑的意识迷迷糊糊的,能感觉白青墨一直再猛亲自己,总觉此人每天早上给她留一嘴口水。
不知为何她最近总感觉有些心神不安,明明日子还是跟往常一样过,但就是有一股不安,这种莫名的烦躁感,让她最近的字都变得轻浮了不少。
今日早上,丫鬟端了一碗莲子百合粥,她正无聊拿着白色的汤匙在红瓷碗碗里乱搅,碗勺碰撞的叮叮声,实在没规矩,好在家里无人敢管她,就任她胡闹,不好好吃饭,用完早膳,照例问一声“孩子如何了。”
杏黄就跟细细说一下孩子的情况,孩子还是那样,吃得少,时常哭闹。听到这里她更加心烦。这和她们说着孩子的事情时候,白兰突然煞白了脸进来,推了推杏黄让她带着其余丫鬟走,等屋子里只有他们杭家人时,杭玉淑道:“怎么了?大惊小怪的。”
“窦公子来了?”
杭玉淑翻着字帖,心里有些紧张,但还是故作镇定道:“窦公子?窦大哥,他怎么来了?他不是一直在外面游历吗?估计是来想问问我和玄哥婚事取消的事情吧。你们先快把人请进来再说。不要多嘴,我来应付。”
白兰满脸惊慌忍不住叫唤道:“是窦玄公子,窦玄公子来了!外面仆人通报,我还不信,自己隔着门缝偷瞄了一眼,是窦玄公子!”
杭玉淑话还没有听完,猛得一下就站起来,话都再发颤,“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不是都死了吗?就算活着,为何我没有收到一丝消息。一定是个骗子。铃兰白兰你们再去看一下。”
“完了!彻底完了!我要死了!”她哭出了声,浑身火热,额间冒出冷汗,又不停打颤。在屋内不停左右踱步,比起窦玄回来的喜悦,她更多的是害怕,是被捉奸在床的害怕。“死“后立马再嫁他人,窦玄回来了一定会“杀”了她的。
丫鬟们急匆匆跑来,“没错,是窦公子。”
“让…让他进来,白兰霜兰你们出去找白青墨,想办法,让他晚上别回来了实在没办法就……晚点回来。”她连话都打哆嗦,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此时她虽然慌张害怕但是脑子却异常清醒,“香兰,帮我把白府的丫鬟都遣到旁屋去做事,特别是知道窦玄来了的看门仆从,铃兰,你去领着窦玄到西边堂屋客房,我在那里等他。”
吩咐完一切,杭玉淑独自在厢房等待,手里的帕子都被揉皱了,外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她再也等不下去了,腹中的任何说辞,再见到窦玄的那一刻,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便先决堤,快步奔向他,窦玄很自然的将人搂在怀里,玉淑勾着他的脖子,比问候的话先来的是玉淑的哭声。
欣喜,害怕,彷徨,无奈所有的情绪都藏在她的哭声里。
“你还活着……”
“活着……活着的每一天我都很想你……”
泪目里模糊透露出熟悉的面容,她双手颤抖地轻触他的脸,心痛道:“你怎么变这么瘦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