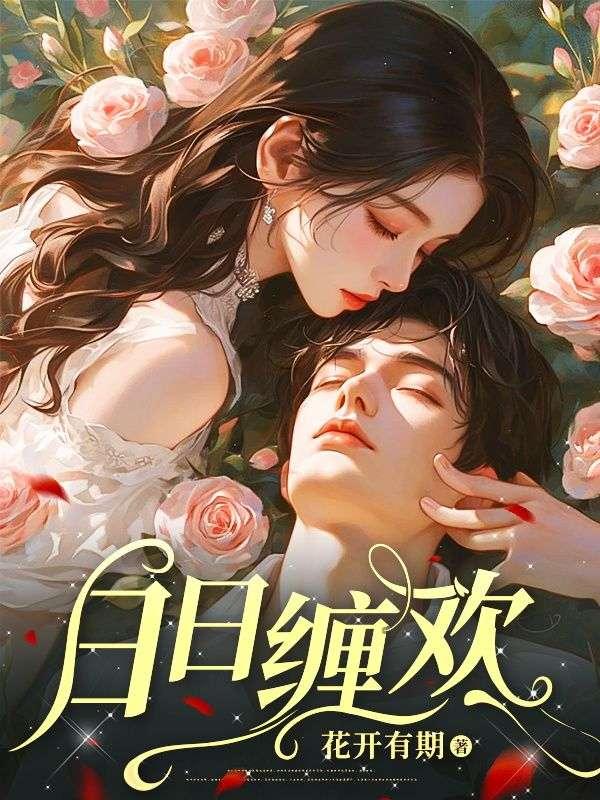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七重梦境 > 第 72 章(第2页)
第 72 章(第2页)
许久,久到林晚几乎以为信号已经彻底中断,夏禾的声音才再次传来。
她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兴奋雀跃,也不再是往日那种不管不顾的冲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林晚从未在她身上听到过的、如同雪山融水般沉静、却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力量。
“老女人,”她的声音透过风声,清晰地传来,“帮我转告那个叫朱利安·克罗夫特的老头子。”
“什么?”林晚下意识地反问,以为自己听错了她语气中的决绝。
“我说,”夏禾一字一句地,异常清晰地说道,每个字都像刻在石头上,“我的作品,不会离开这片土地。一件也不会。”
林晚愣住了,季然皱起了眉,连苏晴也掩住了嘴。
“我的艺术,从里到外,都属于这里。”夏禾的声音平稳而有力,带着一种落地生根般的笃定,“属于这片终年不化的雪山,属于这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属于这些脸上有着高原红、眼神像星星一样干净的牧民,属于扎西,属于学校里那些孩子们……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阵风,每一缕阳光,都是我现在的作品里,不可或缺的呼吸和心跳。威尼斯……太远了,也太……‘干净’了。那种被精心布置、一尘不染的展馆,那里安放不下,我的‘神’。我的‘神’,就在这里,在冈仁波齐的风里,在玛旁雍错的湖水里,在每一个虔诚的转经筒里。”
“但是夏禾,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威尼斯双年展!是无数艺术家梦寐以求的……”林晚试图让她明白这个机会的重量。
“我知道。”夏禾平静地打断了她,没有激动,没有犹豫,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我知道,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好的机会,是通往‘成功’的捷径。但,对我来说,已经不需要了。”她在那头,似乎轻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超脱的释然,“我已经不需要,再向任何人、任何所谓的权威殿堂,去证明我的艺术的价值了。我的价值,由这片土地定义,由我自己的内心确认。”
然而,她话锋一转,语气里忽然又注入了一丝熟悉的、带着野性和狡黠的笑意,像高原上突然掠过的一抹顽皮阳光。
“不过嘛……你帮我,给那个眼光还不错的老头子,带一句话。”
“什么话?”林晚下意识地问,心跳莫名加速。
“你就说,”夏禾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挑衅的、却又无比真诚的邀请,“如果他,真的像传说中那样,追求最极致的‘真实’,真的想看懂我的作品。就请他,收起他那套威尼斯的绅士做派,亲自,来这里。来这片,平均海拔五千米以上的、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来呼吸这里稀薄却纯净的空气,来感受这里能把人骨头吹透的烈风,来用他剩下的那只眼睛,亲眼看一看,什么是比任何白色立方体美术馆里,都更宏大、更残酷、也更壮丽的,活着的艺术。”
“我会在这里,等他。”
说完,不等林晚再有任何回应,电话信号发出一阵刺耳的忙音,随即,彻底中断。
林晚握着那只只剩下单调“嘟嘟”声的手机,久久地,僵硬地站在原地。办公室内一片寂静,落针可闻。
她不需要再看向季然和苏晴,也能感受到她们眼中与自己相同的震撼。
她知道,电话那头的夏禾,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她们时时担忧、需要工作室作为庇护所的、才华横溢却冲动不安的女孩了。
她,已经用这片高原赋予她的力量和智慧,成长为了一个内心无比强大、艺术信念坚不可摧的、真正的艺术家。
她甚至没有拒绝机会,而是用一种更高级、更骄傲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游戏的规则。她向那个远在威尼斯的、传奇的策展人,掷地有声地,下了一封来自世界屋脊的、带着风雪与阳光气息的战书。
这封战书,无关名利,只关乎艺术的本源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