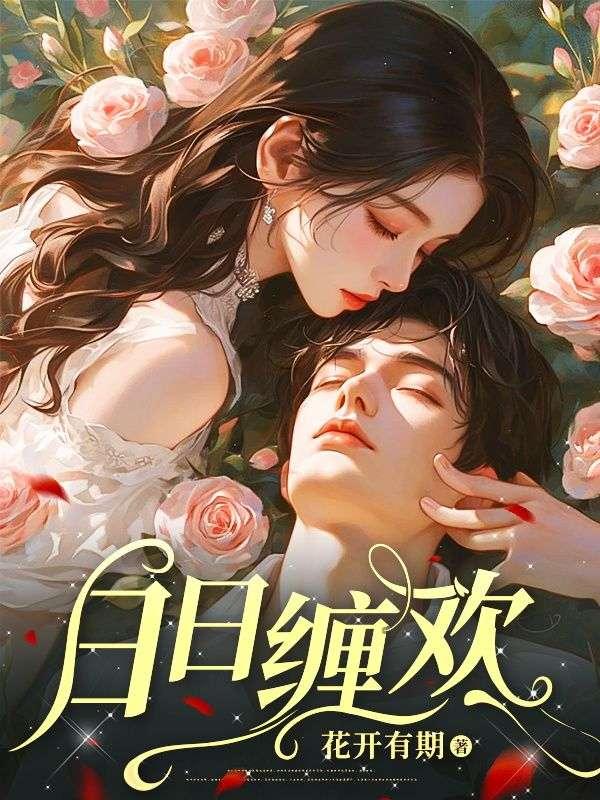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大虞女战神的废材儿子(大虞艳母传) > 第58章 夜宿皇宫(第1页)
第58章 夜宿皇宫(第1页)
大红宫灯在精雕细刻的廊柱间投下晕染的光圈,本该喧腾鼎沸的皇宫此刻却笼罩在一片刻意营造的、近乎死寂的“庄重”之中。
没有礼乐喧天,没有百官朝贺,没有万民瞻仰,甚至连最基本的皇室仪仗都精简到了寒酸的地步。
通往内廷的甬道空荡得能听见风声穿过戟架的呜咽,只有两列身着玄甲、面覆铁盔的龙镶卫像雕塑般矗立,他们的存在不是装点,而是冰冷的威慑。
尚书令管邑、闽浙总督谢安石、内务大臣沈墨轩……这些以“清流”、“节俭”、“祖制”为旗帜的文官领袖们,这次罕见地拧成了一股绳。
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国用艰难,不宜铺张;江南初定,大婚宜简;更暗指若过分张扬,恐坐实“权臣以母惑主、败坏纲常”的天下骂名。
每一句都引经据典,每一句都站在道德制高点。
我纵然权势滔天,也无法全然无视这股凝聚起来的“舆论”力量——至少在明面上。
于是,这场注定要载入史册(无论以何种方式)的婚礼,便被压缩成了眼前这幅诡异的图景:空旷得有些渗人的内殿,仅有的见证者是我,身着不合身大红礼袍、脸色僵硬的少年天子虞昭,凤冠霞帔却难掩眉宇间一丝愠怒与冷艳的母亲妇姽,以及一个老得几乎站不稳、声音发颤的司礼太监。
殿内只点了必要的烛火,光影摇曳,将人的影子拉长、扭曲,投在冰冷光滑的金砖地面上。
空气里弥漫着陈年香料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灰尘气味,丝毫没有喜庆应有的暖融。
母亲显然极不满意。
即便隔着厚重的皇后礼服,我依然能感觉到她周身散发的低气压。
那身按照最高规格赶制出的礼服穿在她近两米的巍峨身躯上,依旧显得紧绷,尤其是胸前与臀股处,锦绣云纹被撑出惊心动魄的饱满弧度,金线刺绣的凤凰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仿佛随时要活过来择人而噬。
她描画精致的眉眼间,没有了平日刻意流露的慵懒或媚意,只剩下一种冰冷的、被冒犯的威严。
但她也清楚,在这件事上,我的“妥协”是必要的政治姿态,她的个人意愿,无论多么强烈,都必须让位于更大的棋局。
因此,她只是用那双琥珀色的眸子冷冷扫过空旷的大殿,鼻腔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轻哼,便不再言语,任由那老太监用干瘪尖细的嗓音,拖着长调,进行着简化到极致的仪式。
“一拜天地——”
虞昭几乎是被人推着转过身,对着虚空敷衍地弯了弯腰。
他身上的龙袍改制而成的吉服显得宽大而可笑,衬得他越发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
他脸色苍白,嘴唇紧抿,眼神里充满了屈辱和一种近乎麻木的茫然。
母亲则站得笔直,仅仅是象征性地颔首。她高大的身躯在这一刻显得极具压迫感,仿佛不是她在拜天地,而是天地需要仰视她。
“二拜高堂——”
高堂位置空置,只有两把冰冷的紫檀木椅。两人对着空椅再次行礼。虞昭的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母亲的红唇勾起一抹极淡的、嘲讽的弧度。
“夫妻对拜——”
这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刻。
当虞昭僵硬地弯腰时,母亲不得不微微屈膝,并极大地俯下身,才能与他在形式上“对拜”。
她那一头如瀑青丝从凤冠两侧滑落,几乎要触及地面,胸前的巍峨山峦因这个动作而更加凸显,领口处露出一片惊心动魄的雪白。
虞昭的视线正好对上那深渊般的沟壑,他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闭上眼睛,耳根通红。
“礼成——请新人饮合卺酒!”
老太监颤巍巍端上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两只小巧的金杯,用红绳相连。合卺酒,本该是甜蜜的缠绵,此刻却像两杯苦涩的毒药。
母亲直起身,优雅地端起其中一杯。
虞昭的手指有些发抖,几次才握住杯子。
两人靠近。
身高差再次成为无法忽视的障碍。
母亲只得又一次弯下那傲人的腰肢,修长脖颈低垂,才能将手臂与虞昭持平。
她的脸庞靠近他,吐气如兰,红唇几乎擦过他的额角。
虞昭浑身僵硬,连呼吸都屏住了,只能被动地抬起手臂。
金杯相碰,发出清脆却孤零零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