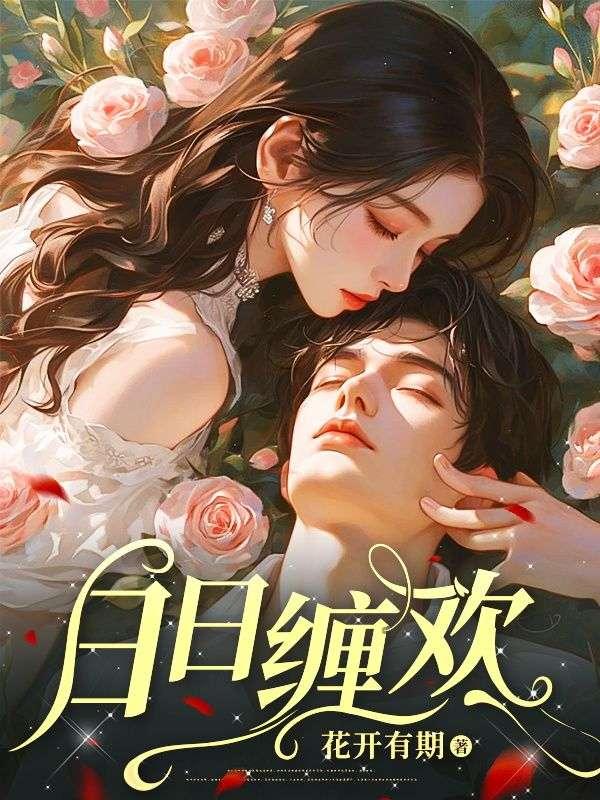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使命召唤/COD乙女]Y/N是个外星人 > 第五十七章(第2页)
第五十七章(第2页)
他开口,像是把那些沉的东西又咽回去了,只留下一点余音,在她额前萦绕,“我十几岁……就上战场了。见过太多生死,眼睛都看麻木了。这双手沾过的血,洗都洗不净。身上的疤,比我能数清的还多。”
“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还会拥有一些特别的感触。”每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还带着水汽和凉意。
Keegan就这样看着她,目光很深,很深,仿佛要透过她的眼睛,看进YN灵魂里去,又像是透过她,看到了某种连自己都陌生的东西。
“谢谢你。”他说。很轻,却郑重。
YN察觉到了他心底波澜,像一丝线,似乎正想与自己的感知连上,她有些惊讶,这是灵族之间才会拥有的东西,感知互通。
她抬起手,指尖点向Keegan心脏的位置,“为什么谢我?这不是因为我。是你本就拥有特别的特质。”
YN看向他,那双眼像盛着整片星空的幽亮,“在我们灵族里,这就是感知的一部分,只有纯粹的灵魂,才会拥有。与你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YN看见那灰蓝色里忽地漾开了什么,很亮,很快,随即又隐了下去。Keegan没有再说话,他只是垂下头将脸埋进她的颈窝。
手臂收得更紧了,像是要从她的身体里,汲取某种可以对抗过往的东西,又像是仅仅想确认这份存在。
直到傍晚,YN才从他房间里退出来。合上门时,Keegan仍定在椅子里,沉在自己的静默中,不知在找些什么。
YN转身准备去找珊莎,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刚走没两步却被Price叫住了。
“Kid,你去趟楼上,把Krueger捞出来。他还在那间房里。”Price站在走廊那头,嘴里叼着半根雪茄,眼神有些沉。
暗室的门虚掩着,Krueger还在里面,从那日事情了结起,他就把自己关在了这里,门没锁,但他没出来过。
他背对着门,蹲在那堆如今只能称为残骸的东西旁,手里握着匕首,刀刃上糊满了分辨不出颜色的污物。他在动,动作很慢。
那具异化的躯体,在他刀下,被进一步分解,撕碎,蹂躏。露出里面早已变色的骨骼和内脏碎片。
他的眼是红的,是被溅起的血沫,一层层染上去的。脸上,身上,手上全都挂着粘物。头罩也被红渗透,沉沉附在鼻梁和眉骨的线条上,而那双眼,猩红的镶在骨相里。
整个人都裹在腐烂的腥气中,可Krueger不在意。他只是重复着动作,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宣泄,才能弥补,才能惩罚。
“IchwerdedeineKnochezuStaubmahlenundihnindeineeigenenAugenblasen……”(我会把你的骨头磨成灰,再吹进你自己的眼眶里……)
“……wiederundwieder……”(……一遍又一遍……)
当初在死城,YN差点被吞噬时Krueger也疯,也恨不得撕碎一切。可那时的疯没这么彻底,没这么个人化。因为他清楚,哪怕他不愿承认,那东西是另一种规则的碾压,愤怒显得无力,毁灭遥不可及。
可眼前这个总督,这只臭虫不同。是他随便伸伸手就能捏死的东西。可就是这样一个东西,竟敢生出那样龌龊的念头,居然想要染指她。
而自己居然还被摆了一道,让这只臭虫有机会,在自己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把YN当作一件可以炫耀,可以玷污的战利品。
这种屈辱,这种一想到她可能遭遇的亵渎,就快要让他炸裂,让他疯狂,让他自我折磨。
忽地,Krueger听见门被推开,不是风,是人的气息。他头也没回,“滚出去!”
身后没动静。那人没走也没说话,Krueger心头那股邪火,窜得更高。他猛然回身看也没看,匕首掷了过去。
匕首脱手的瞬间,才看清门口站着的人是谁。
是YN。
“该死!”Krueger在看清她的同时,身体就做出了反应,像一头猎豹朝前扑去,准确无误抓住了刀柄。
他抓得又急又狠,掌心的血立刻涌了出来,顺着指缝,滴滴答答,落在脏污的地上。
YN仍没说话,只是走上前,拉住了他的手腕,将人从那间疯屋里拖了出来。
Krueger眼里的戾气没褪,可他并未挣开,就这么任由她拉着,踩着一路滴落的血污,一直来到YN的房间。
YN将他推进浴室。浴缸里,已经放好了大半缸水,这是她特意提前去浅滩打来的,“你太臭了,先洗个澡。然后我给你包扎。”
Krueger只是站着,没动。像还没从疯狂的血腥节奏里脱离出来。手里还攥着那把沾着自己鲜血的匕首,一滴一滴,砸在地砖上。
YN没再催促,她只是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将他的指节从刀柄上耐心掰开。又开始帮他脱衣服。先是最外面那件被血浸透的战术服,解扣子拉开链褪下来,扔在一边,然后是里面同样脏污不堪的衣裳。
指尖不可避免触到他皮肤上新旧交叠的伤疤和紧实的肌肉,YN也不觉有什么。直到她的手移到他腰间,去解战术裤的裤扣时。
Krueger终于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