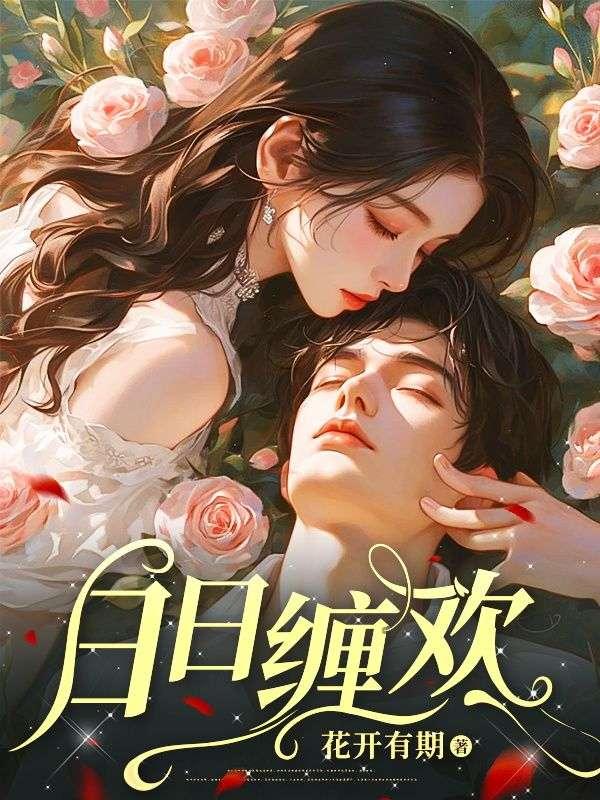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荒山安居日常 > 李干(第3页)
李干(第3页)
黄迎春没有争辩,她深深地低着头,渐渐地红了脸。
旁人以为她是尴尬,或是被气得羞红了脸,其实黄迎春只是不想让人看清她的神色。
黄迎春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这是一个崭新又陌生的世界。
虽然它的生产力水平比现代低下,虽然它不是她所知的任何一个朝代,但是阶级之别是共通的。
哪怕是在人人平等的现代,权力大、财富多的人,往往也会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风景与便利。
她虽然有现代的记忆,但未必会比只活一世的安朝人聪明。
反而,在科技水平不够发达的世界里,兴许能激发出大脑更多的潜力,使人开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最要紧的是,她如今已在深宫,这是一个离皇权最近的地方,也是掉脑袋风险最高的地方。
她要打起十二万分的小心,宁可让人笑话没见识,也不能自视甚高,以为自己可以做成什么事。
伴君如伴虎,苟着才是王道。
终于,黄迎春熬到了出宫,她不用再刻意掩盖自己的见识,因为哪怕有人能通过她的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猜到她的来处,也无人敢打听。
她身上所有不同寻常的行为,但凡有人问起,黄迎春都可以用自己入宫十五年的经历做掩盖。
只要这一句,就无人敢再继续打听。
皇宫是哪里?那是皇帝——天底下最有权势的人待的地方,所以侍候皇上的人懂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那是再应该不过的了。
什么?怀疑?不不不,我只是好奇,你千万别怀疑我,我绝不是奸细,也没想干坏事。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真的不想干坏事!真是,我为什么要怀疑呢?我一个平民百姓,打听宫中的事情,是何居心?我为什么要打听呢?我为什么要好奇呢?这是我该好奇的事吗?天哪,我摊上事了,怎么办?我为什么要开口搭话呢?我这嘴真应该缝起来……
黄迎春只要往皇宫的方向指一指,再高深莫测地盯着对方,皮笑肉不笑地呵一声,上一瞬还在和黄迎春东说西聊的人就会自己脑补一大堆,再也不敢和黄迎春有过多的牵扯。
牙人都是人精,虽然宋大是从乡下调上来的,不如其他长在城里的牙人有眼力见,但他个性聪明,从来不瞎打听。
黄迎春知道火炕和火墙是什么,宋大就不再解释和介绍。
黄迎春不知道永安城里的普通人家冬日都用着火炕,宋大也不吃惊。
黄迎春问做火炕、烧火墙的价钱,宋大立刻细细地给她讲解。
慈善堂里有火炕,但黄迎春租的那间屋子是云娘子喂奶专用的,并没有火炕。在她抱着汤婆子窝在芦花被里的每一个夜晚,黄迎春都在想着她在荒山脚下的新家,新家里的火炕,该是多么的温暖舒适啊!
有了火炕,哪怕烧不起木炭,她也能在冬天过得舒舒服服的。
火炕这么好的东西,黄家村里为什么没有?黄迎春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但她能猜测一二。
对新事物的能力接受最慢的,永远是穷人。
在粮行买粮食和稻种时黄迎春就知道了,农人最要命的缺点,不是贫穷,而是愚昧。
哪怕是明说一定会提高产量的好稻种,也总有人紧紧地攥着自己手里的钱,不肯多花一文,不愿多尝试一种可能,只一味地相信自己的经验,只要自己买了许多年的老稻种——哪怕市面上已经有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新稻种,新稻种的产量比他点明要的老稻种不知高出多少。
黄迎春也穷,好在她懂得变通。
所以当她扛着新稻种兴冲冲地站在新家前,看着监工指着最左的一间屋子说这是堂屋时,黄迎春并没有吵嚷。
中堂中堂,堂屋不该是中间的吗?
黄迎春的疑惑在她看到隔墙相连的火炕和灶台时烟消云散。
为了冷天时能舒舒服服躺在炕上取暖睡觉,也为了省点柴火和力气,堂屋在左边就左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