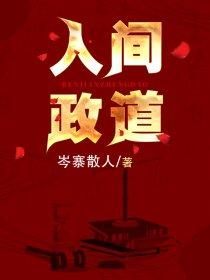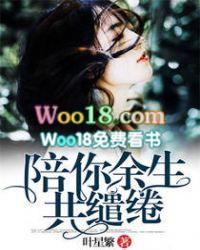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总是被迫成为全场焦点 > 90100(第4页)
90100(第4页)
程序头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比他听过的任何恭维都入耳。他内心一热,突然觉得这个周末临时加班的工作,似乎还不错。
不过他以为自己会很快上手这个案子。
毕竟从资料上看,李青慈刚经历了一场惊险绑架事件,但并没有明显的急性应激症状,也没有严重的情绪失控或自伤倾向。
甚至……程序悄悄观察了他三天。
他洗澡时间规律,进食适量,夜里能睡五小时,没有过多梦魇,每天早上八点出现在花厅,餐后散步十五分钟,途中会对路过的园丁点头,晚上九点准时回房。
太平静了。
但程序知道,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不正常”,而是“过于正常”。
在纽约临床实习时,他见过不少创伤性事件后强迫性重建秩序的个案。当内在世界分崩离析时,大脑往往会用极度规整的外在方式把“生活”拼好。
所以他转而开始记录细节。
例如李青慈的体温调节异常。即便在恒温25度的室内,他也总披着外套,对外界温度有迟钝反应;他的指尖始终冰凉,尤其是午后太阳最暖的时候也仍如此。
例如他偶尔会陷入一种时间感剥离的状态。程序和他聊天时,有几次问到“你上一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你最近一次做梦梦见了什么”,他都沉默许久。
再比如,他从不提那次事件。
不说“绑架”,不说“生死”,不说“逃脱”。
程序不止一次试图从日常话题旁敲侧击,但他回得云淡风轻,有时甚至会转回来问一句“你读研时经历过学术焦虑吗”,把对话绕走。
他很聪明,极度敏锐。每次被试探时,眼神会轻微游移,语气温和但封闭。而这些恰恰说明他记得一切,只是选择了不说。
程序试着调整了介入方案。
他在花厅东南角支了一个不大的灰色帆布帐篷,内部用天然麻布和软垫隔出小小的弧形空间。帐篷顶被半透明遮光布滤掉强光,只留下类似阴天云层后的柔光。
他在里头放了两张矮脚藤编椅、一张圆几,角落收纳盒里放了一盒星空拼图、一摞素描纸、一只盛着各色铅笔的陶罐。
空气里浮着雪松混桧木的淡香,恰好是李青慈洗发水里那种微不可察的气息。还有轻微流动的音乐,是柔和、不具歌词的法式轻爵士。
没有香薰蜡烛,没有任何明火或刺鼻气味。整个空间仿佛一个误入的静谧巢穴,是一处极具安全感的安静屋。
他在两人共进午餐时不经意提了句,“花厅东南角新布置了个休息区,那边风小,下午光线好,如果你午后散步时走累了,可以过去坐坐。”
李青慈垂眼舀着蘑菇汤,睫毛在瓷勺上方投下细影,没有给出回应。
但次日下午,程序透过书页边缘看见他略带好奇地走进了帐篷。那之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有时翻书,有时动手拼一两块拼图,更多时候只是蜷在软垫上看光影移动,然后睡去。
程序从不打扰,只偶尔以同样不打扰的姿态坐在另一张椅子上,手边拿着自己的记录本,却不写、不看,只偶尔侧头观察。
他这几日才从助理新发来的资料里确认,导师口中的“特殊”,大概是指李青慈是个明星,公众人物的隐私问题,他们一向需要特别重视一些。
只是李青慈睡着的样子,近乎虚无。跟他在网络上那些视频里的了解到的,很不一样,好像被剥离了什么。
他不自禁伸出手,指尖微颤,职业素养与某种更原始的冲动在神经元之间拉锯。他想要轻轻触碰这人的眉心,来确定眼前人是否真的还存在于人间,而非自己臆想的投影。
那本该睡着的人睁开了眼,看着他问,“程医生,你怎么了?”
程序收回手,有些不敢直视他那双过于漂亮的眼睛,“我……我哪里不对劲吗?”
“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李青慈支起身子想了想,选了一个最贴切的词,“心痛。”
“抱歉,可能走神想到些旧事。我不该把情绪带进工作,影响到你。”
“没关系,心理医生也是人,程医生不用自责。”他把滑落的外套拉回肩头,“我理解。”
“青慈,你……你可以叫我阿序吗?总‘程医生程医生’的,感觉有些生分,我以为我们这些天聊得都很愉快,起码算是朋友了。”
“谢谢你,阿序。”他没有拒绝,目光扫过帐篷顶垂落的流苏,又看了一眼这个总是很有朝气的青年,“布置这些费心了。”
“不……不用谢,应该的。”程序总会为自己无法在他面前保持长久的专业面貌而感到懊恼。
李青慈屈起膝盖,“阿序,你在哥大那几年,有见过人死在你面前吗?”
程序内心起了波澜,这是这几日以来,对方第一次主动在他面前提起这件事。他没立刻回应,喉结滚动一下,才问,“你是说……自然死亡,还是意外?”
“都算。”李青慈望着帐篷外的花,“你当时会觉得,那个瞬间有声音吗?有风吗?还是很静?”
程序沉回想了一下,“我听过心跳停下来的声音,是监护仪的‘嘀——’,那种平直的长音。”
李青慈没有接话。他只是慢慢地,把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指尖互扣,像在试图确认自己还存在于一个温度正常的空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