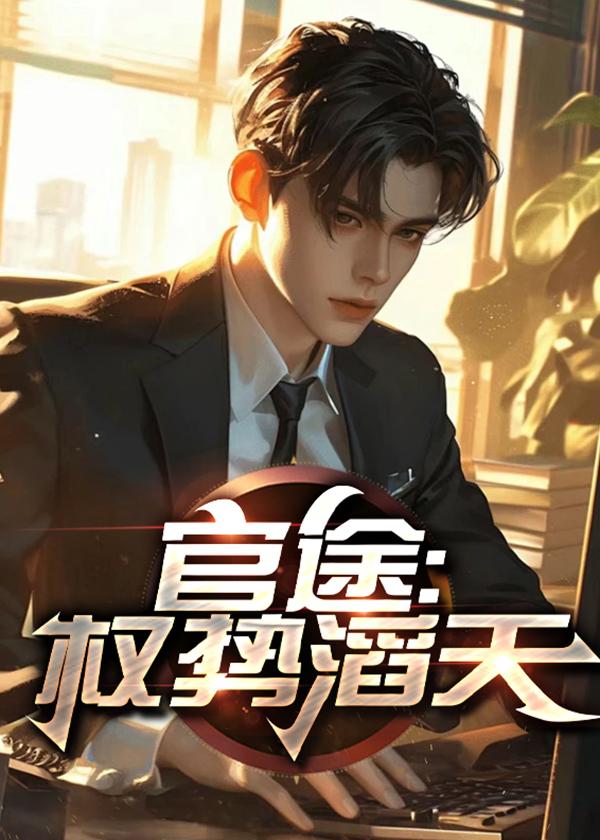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都重生了,谁还当演员 > 第776章 巨人倒下时身上还是暖的(第1页)
第776章 巨人倒下时身上还是暖的(第1页)
李明洋站在自己的角度,给刘师师分析了一下好莱坞和东大电影的老大,老二关系。
然后着重分析,黎冰冰的人情世故和才华横溢。
听的刘师师一愣一愣的。
“好复杂啊!”刘师师抱头痛哭道。
。。。
火车到站时,北京的天空正飘着细雨。杨蜜拖着行李箱走出出站口,雨水顺着屋檐滴落在她肩头,像某种久别重逢的轻语。她没有打伞,只是把外套兜帽拉起,任凉意渗进发丝。城市依旧忙碌,行人低头疾行,耳机里放着各自的歌,仿佛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剧本里。
她步行穿过两条街,拐进一条老旧胡同。巷子尽头是一间改造过的四合院,原本是某位退休教授的居所,如今成了“无声之声”项目的临时办公室。门牌上挂着一块手写木牌:“声音剧场?非营利协作空间”。推门进去,屋里已有人在等她。
李明洋坐在茶几旁,手里捏着一份文件,眉头微皱。见她进来,抬头看了眼:“你可算回来了,财政局的人明天要来听汇报,三百万元的拨款不是儿戏,咱们得拿出具体执行数据。”
杨蜜脱下湿外套挂在衣架上,走到饮水机前倒了杯热水。“数据我路上整理好了,”她声音有些沙哑,“贵州那二十天,我们采集了六十七段儿童独白音频,完成了九场即兴声音剧排练,培训了四位本地教师掌握基础引导技巧。每个孩子都录下了想对父母说的话??有一半内容,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说出口。”
李明洋放下文件,盯着她:“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教育局批了钱,可基层反应冷淡。有校长直接问:‘这能提高升学率吗?’还有老师说:‘你们搞艺术疗愈,不如多捐几台电脑实在。’”
杨蜜笑了笑,坐到他对面:“他们不懂,一个觉得自己不重要的人,再好的设备也唤不醒他的眼睛。我在贵州见过一个男孩,十三岁,三年没跟爸妈通话。问他为什么,他说:‘打了也没人接,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说的话根本不值得被听见。’结果第一次参加声音工作坊,他对着录音笔说了四十分钟??从奶奶做的腊肉味道,说到自己偷偷喜欢班上女生。说完后,他哭了,说‘原来我也能说这么多’。”
李明洋沉默片刻,低声说:“你真打算在全国铺开?三省十二县,两百所乡村学校……这不是慈善,是社会工程。”
“那就一点点建。”她说,“从前拍戏,一场哭戏要NG八次,直到镜头完美。可现实里的痛苦不会重来。这些孩子等不起。”
窗外雨声渐密。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抖了抖羽毛,又飞走。
第二天上午,财政局三位工作人员准时抵达。会议室墙上贴满了项目进展图:地图上插着彩色图钉,代表已覆盖地区;另一面墙则是孩子们的手绘信件复印件,字迹歪斜却用力。
汇报开始后,杨蜜没有用PPT,而是播放了一段音频。
那是贵州山村夜晚的录音。风穿过山谷,远处狗吠零星,接着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带着怯生生的笑意:“爸爸,妈妈,今天我和杨老师一起煮饭啦!我切菜了哦,虽然切得不太整齐……但我没有烫到手!我还学会唱《小星星》了,你要不要听?”
琴键响起,稚嫩的歌声缓缓流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房间里静得能听见呼吸。
一位女评审员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轻声问:“这是真实录制的?”
“原始素材,未经剪辑。”杨蜜答,“我们不做美化,只做记录。每一个声音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努力确认自己存在感的生命。”
另一位男评审员翻看资料,忽然抬头:“你说已在试点培训‘声音引导员’,但他们本身也有创伤吧?如何保证他们不会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
“这正是我们设计督导机制的原因。”她打开笔记本,“每位引导员每月接受一次线上心理支持会议,每季度轮换区域交流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追求‘治愈’,只追求‘陪伴’。就像点灯,不需要照亮整条路,只要让对方知道黑暗中有人同在。”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最终,财政局表示将按计划拨付首笔资金,并建议申报国家公益创新奖。
送走客人后,李明洋靠在门框上看着她:“你越来越不像演员了。”
“本来就不该像。”她收拾文件,“演员的任务是让人相信假的。我现在做的事,是要让真的被看见。”
傍晚,她独自去了东城区一家社区活动中心。这里是“声音剧场”城市延伸计划的第一站,专为在京务工家庭子女开设周末课程。今晚是第一次公开演出,主题叫《等一个人回家》。
场地不大,几十张椅子围成半圆。观众大多是农民工家长,穿着工装或外卖制服,脸上带着疲惫,但眼神期待。
灯光暗下,音乐起。
第一个节目是由八个孩子共同完成的声音装置《电话铃响七次》。舞台上空无一物,只有七部老式座机并列摆放。孩子们轮流拿起听筒,念出真实的家书片段:
“妈,我想你做的红烧鱼了……”
“爸,弟弟昨天摔跤了,我没抱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