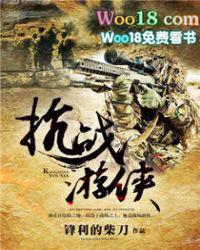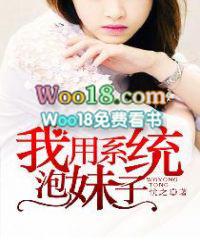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皇叔且慢 > 第六百九十四章 修渠一事(第1页)
第六百九十四章 修渠一事(第1页)
听闻是要重修永济渠和淮南水道,在座诸人也明白了过来,也是,若说他们。。。除了李煜之外。。。还有共通点的话,那便是对水利或多或少都沾那么一点。
“漕运关乎国计民生,还望诸位畅所欲言!”赵德昭见他们谁也没有开口,又补充了一句道。
杜镐闻言起身,朗声道:“殿下,下官不曾治过河道,不过就是研究了些史料,也不知说的有没有用处。”
“无妨,你且说来!”
“下官以为,治水当先明其源流,永济渠自隋炀帝开凿,历唐至本朝,屡修屡淤,下官曾考《水经注》,知此渠易淤之因,在于黄河泥沙冲击,若要长治久安,当仿汉时‘引清济浊’之法,于上游分引清水冲刷河道。”
赵德昭点头,遂即道:“杜校理博古通今,此言甚善,只是如此一来,工程浩大,如何调度?”
杜镐转头看向乔维岳,“具体实施,乔大人要比下官知晓得多!”
乔维岳闻言瞪了杜镐一眼,他一个知其理论的说起来简单,可具体实施,却是难的,他倒好,直接甩给了自己。
“下官记得,乔维岳在江南时,也曾为淮南转运使,好似曾改良过水闸?”李煜突然开口道。
乔维岳忙躬身道:“是,下官依据运河水量改良水闸,可让漕船通行时逐级升降,省却拉纤之苦,今永济渠淤塞,下官以为,也可分段疏浚,并设复闸以调节水位,如此,既免泥沙沉积,又利舟楫通行。”
乔维岳说着转头看了几眼,见没有笔墨,说道:“下官届时可将图纸画出,何处设斗门,何处拓宽河床,若辅以杜大人‘引清济浊’之法,想来定事半功倍!”
“《唐六典》有载,昔年修漕渠,须调民夫十万,耗粮五十万石,今若仿效,需先核算国库能否支撑吧!”说话的是赵德芳,他今日得了皇帝的话,也去了趟工部,将曾经修河道的记载翻了不少,其中都记载了修渠花费,可都不是小数目。
“下官建议可分三年施工,先疏浚要紧河段,再逐步完善,以免劳民伤财!”杜镐说道。
“耗费问题,届时得由你们出了方案计划之后才能核算,先不说这些。”赵德昭对于大宋如今的收入是有信心的,若实在紧张,那就先修永济渠,淮南其余河道缓一缓再说。
先提出建议的都是原江南国的人,眼看着连李煜脸上都多了几分笑模样,胡思进和罗处约二人对视了一眼,心想他们吴越水系也多,不就治个河吗?有什么难的!
“殿下,”罗处约起身朝赵德昭拱手,“下官有一法,或可助乔大人精准测定河床淤泥深浅,名曰:水平测淤法。”
“哦?还请详述!”不说赵德昭,便是乔维岳都来了兴趣,这名字他可没有听说过。
“还请殿下给下官一张笔墨纸张!”罗处约道。
赵德昭朝宫人挥了挥手,很快有人取来所需之物摆放在罗处约面前,他拿起笔勾画河床剖面,解释道:“永济渠年久淤塞,但各处深浅不一,若盲目疏浚,或挖浅不足,或掘深过甚,徒耗人力,下官此法,乃借水行平处之理,以木制测具,量河底淤泥。”
说完,罗处约也已经在纸上画完,他指着图纸道:“取轻质硬木,制成长杆,杆上刻尺度,顶端系小旗,于两岸立桩,拉绳为基准线,确保测量时绳平如准,而后,将浮标垂直插入水中,直至触底,观察水面所淹刻度,即可知该处淤积厚度。”
乔维岳和杜镐二人懂河道治理,故在罗处约说完后,他们已是大致明白如何操作,但赵德芳站在一旁却是看得皱眉,罗处约又看了一眼赵德昭,见他神情平静,看不出什么来。
思考了一瞬后补充道:“具体施行时,可将疏浚河段每百步设一标记,编号记录,测淤时,二人立于船侧,一人持测杆垂直下探,另一人记录刻度,每标记处测三次,取均值,以防误差,最后将数据汇总,再标注何处需深挖,何处可浅疏。”
这法子,较传统目测估挖来说更为精准,避免无效施工,同时更能节省人力,若按照他这么说的话,赵德昭在心里默默算了算,测淤仅需小船两艘,测杆十条,记录小吏两人,三日便可测十里。
“妙哉!”乔维岳抚掌大赞,“昔年治淮,下官尝苦于淤测不准,罗大人此法,补我之缺啊!”
杜镐点头,“若辅以《太白阴经》中测平技术,或可更精。”
“好,那便请诸位详细给出图纸以及施行计划,我会让户部算出耗费,具体再行商议。”赵德昭点头。
“殿下,”胡思进哪里能落后,此刻也抱拳朝赵德昭道:“殿下,治水需人力,若全征民夫,恐误农时,下官请调厢军协助,既可监工,又能防河工懈怠,另外,下官也愿派兵巡视河道,以防水匪,保漕运畅通。”